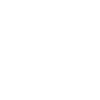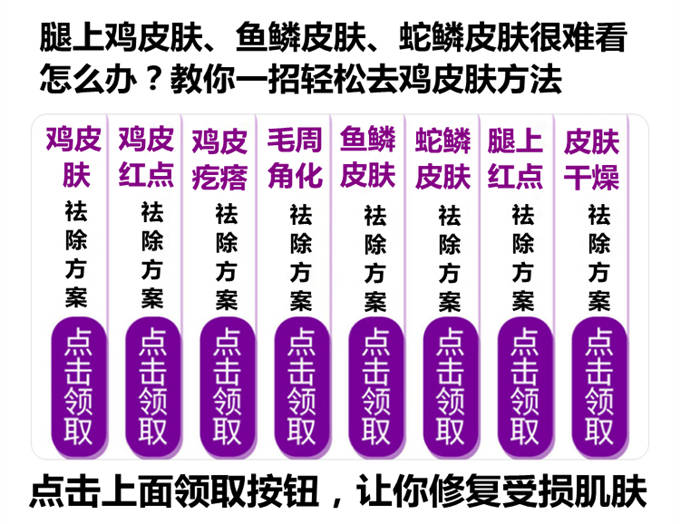我家添章屋场的九间土砖茅草屋,正三间,工具各批三间。老死板的民俗习惯是,右者为尊,我大爷爷和我大奶奶就往东边橹台房里,中央 的批房,是我大伯父茅根和大伯母黄连的婚房。
我大伯母黄连默默地扯着茅根那件粗黑大布缝的衬衣角子,就是不愿松手,我大伯父的心儿,胆儿,肝儿,肝儿,肠儿都溶化了,化得像我们家耕作的卢丘田角上沤着的氹子荡里的软泥巴。我大伯轻轻地捉住 我大伯母微微发抖的、瘦削的肩膀,一口口急促促热乎乎的气体喷在我大伯母的脖子上,我大伯母感受到有点微弱的痒意,心中的一江春水,在眼光中荡起泛着星光般的涟漪,我大伯就像划着渔舟子的艄公,在二个眼睛的湖里“咿呀咿呀”前行。
我大伯轻声说,“哈巴妹妹,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你担忧什么呢?”黄连双眼马上通红通红,眼泪像山中的春日灵溪,漱石般地流下来。就是不语言 ,不松手,仰着头,痴痴呆呆地望着我大伯父。我大伯像是走了二个魂,五个魄,说,“你怎么不信托 呢?”这口吻 ,明确 是想哄我大舵姊的四五岁的女儿公英。“到谷水街上,我给你买一盒丰糕回来尝尝鲜。”
龙城县做得丰糕,用米、粉、面粉掺着蔗糖烘焙的,长三寸八分,宽一寸八分,厚一分,通体金黄金黄,格外香酥,通常 里走亲探友,提一盒贴有窄窄的红纸条的丰糕,那才是倍有体面 ,那叫脱手大方呢!
我们昔阳塅里,没有丰糕哄欠好的夜哭郎。
我大奶奶心细,在隔邻房里,听到一点新闻 ,就出来打圆场,说,“茅根哎,你买丰糕就多添一盒呗,可怜你大姐家的小儿子,芡实,才七个月就没奶水吃,逐日 里拿点米粉糊糊,哄他的瘪肚子,饿得黄皮寡瘦,活像饿了五百年的石猴子!”
我大伯本想这样子回复:做好事啰,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十二个时间 ,我口袋里都是布贴着布,几时装过硬当当的铜板呢?虱子蛋蛋都没有几个!更莫提银光闪亮的银元宝!况且,鸡令郎能当马儿骑着走吗?我花这么大的资源 ,一次买二盒丰糕,那是王侯将相、巨细姐、阔太太消耗 的工具,我们穷苦人家,做好事啰,嘴巴角上打二个巴掌,打死那馋虫子!拿买二盒丰糕的钱,可以买十来斤糙米子,配上沿儿浸水坛子腌的干柴巴叶菜,客栈 里的干红薯米,采些野芹菜、荠荠菜、婆婆丁、野笋子、地衣菜,汤汤水水,稀稀拉拉,迁就迁就,能对服一家人一旬的肚皮呢。但一看到我大伯母眼泪漱石的样子,我大伯的心就隐约 地痛,帖板牙一咬,心横下来,就应承了我大奶奶。
当轿夫是三日脚板、四日肩膀的苦活。阿魏痞子瘦得像雪中的枯木枝头,连人带轿才一百四五十称,我大伯父茅根和二伯父瞿麦抬着,像提着元宵节耍花灯时那盏鱼泡皮灯,似乎没什么重量。
中昔阳在一片氤氲之中。大雨马上要来临,燕子和蜻蜓都在低低地欢快地穿梭,空气中全是 浓郁的金银花的香味。
阿魏痞子习惯于从添章屋场步行到响堂铺药店门口,才肯上轿子。响堂铺药店的十字路口,通常 里,拴马石条凳上,坐着一群闲男子 ,东扯葫芦西扯叶地聊着天。阿魏痞子喜欢和每个闲男子 妻子 娘们作个揖,算是给足了众人的体面 。
轿子沿着戎马大道,过了生发屋场,胡家塅屋场,斋里屋场,逐步 地隐入烟雨之中,不见了。
我大伯母黄连,她这样思忖着:若要是跟在轿子后面,强忍着泪水,看着我大伯父他们远去,怕的就是响堂铺的闲人们笑话;若要是不送一段,心里格外的舍不得。她小脚丫乱跑,往东的胡麻台、蓬家台小路上斜插已往,看着我大伯父的轿子,过了三槐庄前莲花池屋场。莲花池中,那里 是开着一朵朵鲜艳欲滴的荷花啊,明确 就是一大群少女,在微雨中轻歌曼舞。
我大伯母看得痴了,坐在小溪流上的石拱桥栏上,雨丝喜欢在她的脸上写着竖板的小篆文字;她的泪水,把雨丝写的小篆文字,扩大,而又快速模糊掉。
阿魏痞子这号人物,不仅仅在龙城县三十七都永乐乡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神童湾的涟璧书院,在长沙府的岳麓书院,甚至在政界、教育界,亦是台甫鼎鼎。我大爷爷与他结为八拜之交,几多有仰慕的因素 。
阿魏痞子出生在书香门第,少年时间 中过秀才。那时间 ,他的叔父在湘军里当将军,厥后在浙江巡府手下谋得一个的副职。他叔父深知,阿魏痞子是人中龙凤,早早替他运作来一个杭州临安候补知县。哪知道阿魏痞子肩负一卷,雨伞一撑,一声长啸,头也不回,去了日本,喝了三年洋墨水。
厥后,我听我的娘老子在六月的夜里讲阿魏痞子的故事,是这样的:他从日本回国后,与他重新疆喀什府二品大员告老回籍的叔父,关起门来,二小我私人 争吵了三天三夜。阿魏痞子说到激动之时,经常是手舞足蹈,唾沫横飞,“为已谋一生之富贵,鸡犬耳!谋一域一族之富足,镜花水月耳!谋救国救民之计,方热血人耳,方真君子耳!”他拍着胸口,说,“方今积弱积贫之国,救亡图存,唯教育耳!一人醒,至三人醒,三人醒至万万人醒,群情汤汤若长江之汹涌;一人一篝,暗夜观之,若萤虫之火,万篝齐举,若云霞之灿灿耳!一声若蚁,百声若惊鼓,万声齐呐,则若雷霆可震寰宇耳!”
“教民育德,当以经世致用,当以实事求是,当以血性,启民智,唤民心,聚民力,兴实力,富穷人 ,则可鼎国力。”
“悲呼!现在 外夷践门踏户,杀人如麻;内患狼奔豕突,狼烟血腥。吾自长歌当哭,国危,则民跪。吾之乡党,何以站着?”
阿魏痞子对着一天星月,磕了三个响头:“救吾民,救吾国,才是吾之志矣!” 叔父扶起阿魏痞子,仰天长叹一声,“孺子可教矣!吾当玉成你。”
二人商议,将慈禧太后犒赏 的、位于澧州府华容院子一千亩上等水田,一次性卖出,择了昔阳塅蒋家堂、白石堂、茅屋街一带,一百亩荒地,兴建秋实学堂,到了民国三年,改制为整日 制高品级中学。
澧州府华容院子稻田,我大爷爷枳壳、二爷爷陈皮、大伯父茅根、二伯父瞿麦,他们去做过扮禾佬的,自然晓得,那是上等的肥肉子田啊!一年双季稻,四四方方一丘,一丘就有十来亩,完全不是昔阳塅里的梯田,什么斗笠丘,簑衣丘,牛打滚丘,鸡啄丘,狗撒欢丘,弯弯曲曲,像什么样子啊?
那里 的水田,不用沤氹子荡,不用烧火灰,不用施牛栏粪,猪粪,狗粪,鸡粪。冬季种上红花卉子,二犁二耙,腐烂了,全是肥。收完第一季,稻草还田,也是肥。不用担忧天旱,隔邻偌大一个洞庭湖,还怕没水灌嘛!
吃了元宵酒,功夫自然到了手,插上秧苗,扯几回稗子、野慈菇草、四方格子草、水草子、游草子、鸭舌草、烫舌子草,到了小暑,就等开镰。这个时间 ,一群群扮禾佬,打着光脚板,自然开拔到这里来。
响堂铺药店的东边,有一口三角形的水塘,一亩三分地的面积。从上昔阳河中垒的拦河二坝子,叫贺家坝。清亮 的坝水沿着六里长的沟渠,自西向东,汇入三角塘。梅雨季节,从直冲水库,牙塘,上鸦雀塘,下鸦雀塘,安门前塘冲下来的山洪水,也在三角塘汇合。
三角塘是个过水的塘,自然不能养家鱼。可里边野生的小杂鱼,鲫鱼,白条,鳑鲏,溪石斑,翘嘴,麦穗,爬沙鲛,多的是。白条喜欢像箭一样在水面上急渡,正是无风起的三个浪。绿色的小翠鸟藏在柔柔的柳条中,一忽儿钻进水中,叼着一条花花绿绿的、扁扁的小鳑鲏,二只眼睛望着闲男子 们,似乎在问:鱼,你们吃?照旧不吃?你们若是不吃,我就不客套 了!可怜的小鳑鲏,横在小翠鸟的嘴里,放肆的摆动着身体。
三角塘的出水口,双方 安放着用花岗石凿着二寸宽槽口的竖石,中央 是一块湿松木板合钉的闸板,水浸千年松嘛!通常 里,闸板是关着的,要保证田里浇灌。只有到了洪水季节,闸板才会提开。水流若是急了,没有四五斤臂力,那里 提得起哟! 紧迫 时间 ,扯闸板,只有我大爷爷这号人物,才气做获得。
我大伯母黄连,抱着芡实,站在响堂铺药店门前回廊的楼板下面,眼睛却还在痴痴地望着东方。似乎,空中飞翔的燕子,都是我大伯父的身影,在低飞,在盘旋,都在召唤着我大伯母的名字。芡实一直 不住在怀中翻腾,号哭。我大舵姊金花着实 看不外眼,怒斥着不懂事的儿子,“我宿世 造了什么孽哟,生下你这个翻天太公!”芡实看到娘老子,哪晓得什么安危,蹦哒着往母亲怀里爬。金花慌忙接住,芡实把头枕在母亲肩膀上,干嚎几声,睡着了。
我大奶奶慈菇总是担忧着我大伯母黄连,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到了吃中饭时分,还未看到黄连的身影,扯着嗓子喊我七舵姊紫苏,“七妹子哎,快喊你嫂嫂回家用饭啰!”那时,我七舵姊紫苏,古历二月十五月花朝节,刚满十二岁。她正在半月形的灶台上炒菠菜,还要在灶膛中添柴火,忙呢。 我七岁半的父亲,我们那里的民俗习惯,叫爷老子,他忙说,“我去接嫂嫂。”
我爷老子一起 飞跑,到响堂铺药店,没看到人,晓得我大伯母黄连在我大舵姊金花家里。过了王麻子的铁匠铺,前面的小圳巷子边,就是我大舵爷常山的家。
我大舵爷与我大舵姊头胎生的女儿,一个四岁多一点的小孩子,像个喜雀子,更像个禾雀子。最喜欢围着我爷老子转,嘴巴像抹了蜜,细娘舅 ,细娘舅 的,叫得格外的甜。着实 ,公英无非就是想和细娘舅 到圳巷子里去捉鳑鲏鱼、鲫板子、红眼泡、泥鳅子、黄鳝筋。细娘舅 抓到鱼,放在木桶里,公英非得一条条的捏死,搅熟,才肯松手 。还不时哈哈大笑,气得我大舵姊,哇哇大叫:“做好事啰!鱼鳞长到肉里去,会得鱼鳞珠的!”公英哪管什么鱼鳞病不鱼鳞病的,只要开心就好。
公英家也是松木板的二层楼房。上面一层,做点歇伙铺生意,下面一层,做点蒸酒打豆腐的小本生意 。我大舵爷常山,天天 大清早,挑着豆腐担子,扯着鸭公嗓子,尖叫,“豆腐逐一 噢!豆腐逐一 噢!”逢到有挑剔的妇人,或者是喜欢嚼午卵筋的男子 ,我大船爷满脸堆笑,“今天的豆腐,比昨天的许多几何了!”天天 重复的,永远是这句话。
我大舵爷常山后面的院子里,长着二棵像楠竹一样滑溜的梧桐树,约莫有碗口粗。原来做甘肃生意的客商,喜欢把骡马拴在梧桐树上,磨掉了不少树皮。现在 做生意的商家少了,树皮也重新长出来,快痊愈了。
我大舵姊的大门口,是三尺六寸宽的戎马大路,大路中央 ,约莫是踏得脚板多了,许多野草,容易 不敢长出来!路的双方 ,长着铁拔难草,星子草,鱼腥草,间或有一二株马齿苋草,胆子大的蝉,将壳蜕在小枝条上。
屋子西边,有一条丈来宽的小河,我们叫它圳巷子。圳巷子两岸,长满了细叶柳,黄荆条子,醉鱼草,一簇簇金银花,就开在树木上,金黄的银白的花,香得令人打喷嚏。三五只细细的、黄黄的青蜓,一二只“嗡嗡”叫的野蜂子,在花花卉草忙碌穿梭着。间或有,一只黑衣蝶,贴着水面,幽幽地寻找着自己的爱侣。
搭在圳巷子上的小桥,是二根青色的石条子。石条子每逢变天前,石头的纹缝上,生出莫名其妙的水珠。人们经常来视察石条子上的转变 ,来判断天气。这令善于观天说地、外号叫做抱鸡婆的老人,大为光火。
一到小满,山塘水满,圳满河满。公英偏偏是禾雀子托生的,稍不留心,小脚扳不知蹿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必须看得紧奏。我大舵姊每隔半柱香时间,就拿三根老黄荆子捆束的细法器,扯着嗓子喊:“公英,公英哎!”前屋喊到后院。公英的奶奶特殊 喜欢教训儿媳妇,“你不要把公英弄丢了哒,小心我把你的野豆子壳壳(脑壳 )扭掉,当夜壶!”但没有人理睬她。
我爷老子去寻我大伯母黄连,公英正爬在梧桐树,用根干的水竹子,戳那些粘在树干上的蝉壳。捡来一串蝉壳,拿到厚朴痞子那里,可以兑几根细细的甘草,嚼事后,嘴里甜甜的。
我大舵姊金花,随我爷老子决明,来到我大伯母黄连眼前 ,我爷老子还没听清她们说了什么话,黄连高一脚、低一脚、水一脚、泥一回添章屋场去了。
我爷老子其时就希奇 了,问我大舵姊,施了什么梅山咒?我大舵姊只是简朴地说了一句话:“老弟嫂,你还不回去?人家以为你是癫子呢。”我大伯母如梦初醒,慌张皇张,迈着小碎步,烟一样地溜走了。
在我所有的父辈这一代人中,我大舵姊最漂亮 ,最智慧;我爷老子最野最顽皮;我七舵姊明确 是个假小子。老死板人说,少娘疼满崽,公公奶奶疼头孙,我们添章屋场的自制,都让我大舵姊金花和我爷老子决明二小我私人 占尽了。
我大舵姊金花,抱着芡实,坐在梧桐树下,心里想着黄连的事,越想越不是滋味,黄连这个细妹子,傻丫头,对茅根这么痴迷,希望茅根对她仔细 点,呵护点,不要做欺越事,亏心汉,辜负了人家小女人!看来,黄连是个风吹草不能动的角色仔!公英抱着芡实,牵着公英,来到外家 添章屋场。
响堂铺药店,到添章屋场,才三百步脚程。公英几番一再 ,才挣脱娘老子的手,像个禾雀子,早早飞远了。
我大舵姊终究放心不下,只得随着公英飞跑。到了添章屋场,公英早在座在二外婆茴香的怀里,指着细雨中疾飞的燕子,问二外婆,“二外婆二外婆,燕子叽叽喳喳,讲的是么子鬼话?”二外婆说,“我又不是燕子,我怎么晓得呢?”
我爷老子说,“公英公英,我晓得呢。”
公英说,“细娘舅 ,细娘舅 ,你快点告诉我哒。”
我爷老子模拟 燕子的声音,说,“借个地方生个子,借个地方生个子!”众人一齐笑了。
我大舵姊金花,对着我大伯母黄连,稍声说,“老弟嫂,你学着燕子说一声,看像不像啰?”
我大伯母黄连,神色 马上像块红布,低着头,回屋子里去了。
这时,雨越下越密,越下越大,茅草屋檐下,很快挂着一帘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