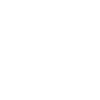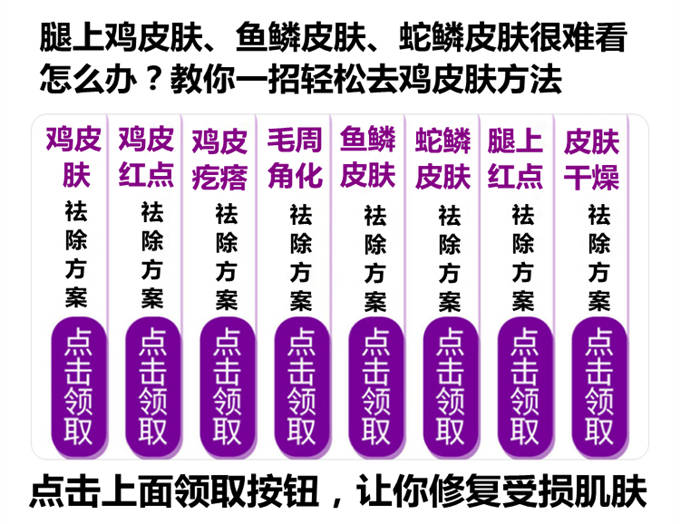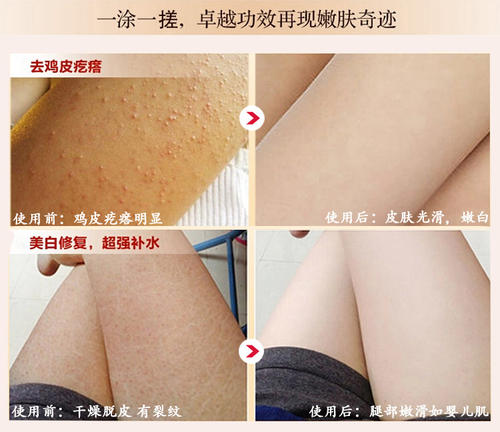
阅读前请点击右上角关注,天天 更新惊险刺激的历险故事!点击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故事!接待阅读,点赞,留言!
这是天下 上最大的一头野猪:体重千余公斤,身长三米开外,黑褐色,毛眼发乌,身上蹭满了松油和沙子。钢板一样,刀枪不入。脑壳 比小型的水缸还粗。钢刀般弯弯的獠牙比筷子还长。闪光乌亮,很是的瘆人。小眼睛像炭火一样的通红。在枯草似的睫毛后面,冷丁一瞅,就足能把人吓晕已往。据猎人们讲:前后有十几位炮手和几十只猎犬在猪王眼前 丧生。同时丧生的尚有 为争取 土地的其它山畜生 ,如黑熊、棕熊、老虎、豹子等等。猪王是森林中的一霸。在猎人眼前 ,猪王为它的野猪家族赢得了最高声誉 。
我见到猪王那是1985那年的炎天 ,我刚刚转业,被局党委任命为柳毛河林场主管生产的副场长。该园地处鹤岗、伊春、嘉荫、鹤北两市一县一局的接壤处,多是朝鲜族住民 ,属于半林半农的两栖单元。解放以前,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副帅崔庸建内相就曾在此恒久栖身 和战斗过。尚有 赵尚志、李兆麟、夏云阶、冯仲云、李延禄等抗联主要向导 人,也曾经在此落脚或休息过。顺柳毛河上行四十里,爬上一座岑岭,那儿就是抗联密营和中共北满暂时 省委的办公处。因此开国以后,许多抗联老战士回忆录中都曾经提到过柳毛河。柳毛河誉满天下,能到柳毛河来任职,做为下层干部,确实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 。
柳毛河在鹤岗市的国界上,又名野猪岭的石头庙子,是该场的第八作业区。因抚育和成林“解放”滞后,第八作业区也就多次在省林业厅生产处被亮了黄牌。成木解放是最后的一道工序,也是最要害的一道工序。一样平常 情形 下栽植的都是针叶的乔木:如红松、樟子松、落叶松、云衫(鱼鳞松)等。人工林长不外自然生长的次生林。必须加以"解放":把上层的灌木砍掉,否则,营林的那部门投资和劳务就算是前功尽弃。全省各大林区,对成林解放这道工序,向来 就是视为重中之重的。省厅亮了黄牌,市局更是不敢怠慢,重复地督促老崔头,尽快的去把那块骨头啃下来。否则,年底评选 ,全省先进企业声誉 称谓就有泡汤的危险。
老崔头叫崔永昌,也是鲜族人。曾经给崔庸建当过通讯 员。因没有文化,以是 ,在场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二十多年。柳毛河是朝鲜族人的天下,也更是他崔永昌的天下。上面派来的向导 ,若是跟他性情 不投,不出三月,就得自动滚开。众人 都说:崔永昌就像那头大孤猪,软硬不吃,刀枪不入,在摩天岭周边一带,他比《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还座山雕。不外,我们俩倒是臭味相投,无话不谈。首先我是他看着长大的,送我上学,送我参军,转业后又把我要了回来,尚有 更深的一层意思:我是他的亲侄女婿,他是我的亲叔丈人。岳父崔永焕和他是同胞兄弟,妻子崔玉珍是他的心肝宝物。有了这些关系,我到柳毛河林场事情,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只要起劲 ,就会意想事成我自动 出击:
“崔场长,现在正是成林解放的最佳季节,我妄想 组织个突击队,以石头庙子为中央 ,用半个月到二十天的时间,把那座“碉堡”,彻底的端下来。我倒要看看,野猪岭上面到底能有几多头野猪,谁人 大猪王又能厉害到什么水平。三军 大交锋,我照旧特等射手呢!”
“也好!”他以父老的姿态赞许道,“你把那支半自动步枪带上。再给你部对讲机,编号是八洞四。我的机子是八洞六,电台开着,有事咱俩随时联系,明天准备,后天岀发。让我年迈 也去,搪塞野猪,他有履历 ,光枪筒子直念不行,那儿是个猪窝,据森调队目测,最少也有个八九百头。真要是惹翻了它们,有个三长两短的,玉珍那儿,我可是没法儿交待啊!”崔场长的眷注,我从心眼里感应激动。
第三天一早,突击队就出发了。东方红拖沓 机牵引着大木爬犁,爬犁上满载着帐篷、行李、生产工具、生涯 用品等等。轰霹雳 隆,阵容 浩荡,沿嘎拉旗河上行。后面是三十多清一色的小伙子,徒步前进,有说有笑,嘻嘻哈哈。我腰别对讲机,肩背半自动,与爱妻崔玉珍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蓝天白云,莺啼燕语 ,河水哗哗流淌,青山一清二楚 。小路蜿蜒崎岖,时而拐到了山脚下,时而消逝 在荒草甸子之中。这条路是恢复前抗联队伍从密营到平原地带的必经之路。
很是的顺遂 ,中午,我们即到达了目的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遗憾的是,我前后左右的转悠了半天,别说是野猪群、野猪王、黑熊、老虎、款子 豹等大的山畜生 ,甚至连个脚印、猪毛、猪粪都没有看到。仅有几只花鼠子,眼睛贼亮,吱吱叫着,蹿到了树上……野猪岭啊野猪岭,那猪王猪群,仅仅是一个漂亮 的传说而已。树都砍光了,人类无处不在,时至今日,野生动物纵然没有根除,生怕 也是三三两两,躲在老林深处惶遽不行终日了。我感应遗憾,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同时也忏悔自己是在虚张阵容 ,肩不离枪,枪不离人。在假设的影子中,那么神经兮兮的随处跟自己过不去……经由 四十里山路的跋涉,躺在铺上,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事实 是大山深处,种种鸟类照旧许多的嘛,唧唧喳喳的,让人觉着心情特此外愉快 。
突击队分成了三个班,以班为单元,在藤条灌木遮得密不透风的山脚下面一字儿排开:镰刀飞翔,斧头闪亮,红旗招展,人欢马叫,时势 热烈,好不热闹。
我是总指挥,玉珍是质量验收员。她从小就在汉语的学校念书,高中结业后考取了东北林业大学的营林工程系。结业后回到林场,可以说是柳毛河土生土长的林业专家了。她长我两岁,身段 苗条,五官规则,举止文雅,言论 大方。作为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十几年的生涯 习惯使她既有鲜族女人的贤慧、矜持、漂亮 、正经 ,又具备了汉族女性的质朴 、热情、勤劳 和阴险 。由于 山里的小咬蚊子太多,她脖系纱巾,上下又加了一层厚厚的蓝色外衣 。现在,阳绚烂 煌光耀,空气闷热,小咬蚊子已经躲起来了,在树荫下面,她解开了上衣的纽扣,那件粉红色的衬衣就很是耀眼的裸露了出来。尚有 那两个馒头般的乳房,像两只受了惊吓的小兔,在衬衣后面一颤一颤地发抖着。我们还没有举行完婚 仪式,自从我转业以后,我们就多次的同居了。崔场长说:“等成林解放竣事 ,就给你们举行一次盛大的完婚 仪式。晚婚晚育,你们俩已经是模范中的模范了!”此时现在,在林荫下面清凉凉的微风中,她鼻尖上有一层红晕在跳跃着,嘴唇微动,火辣辣的眼光 是那么样的迫切而又热烈……我迎着眼光 ,屏住了呼吸,把嘴唇轻轻的迎了已往,嘴唇与嘴唇相碰,是那么甜蜜、激动、温馨、幸福,我含着她的舌头,盯着她的眸子,当游戏向更纵深处生长时间 。突然,扑面 山坡上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召唤声:“野猪!快来呀!一只大野猪!”“哎哟妈呀!这么大呀!快!快!快躲开!快躲开!”人们一齐呼叫呐喊着:“别让它跑了!别让它跑了!整死它,晚上回去打牙祭!”“妈了个巴子的,野猪岭,还真有点玩样儿了呢!也算没他妈的白跑一趟。”“王场长呢?王场长不是带着枪嘛,给它一家伙,野猪肉,别看肉丝粗,可香着呐!”有人就喊:“王明贵!王明贵!干屁的哪儿去啦,领着你妻子 !”他们一喊,我们俩的激情也就突然地消逝 在茫然中,既惊喜又失踪 地说:“走!咱们看看去!”
我背枪爬了上去,玉珍步步紧跟。边走边提醒我道:“你可不能胡来呀!这野猪岭,邪着呐!”
阅读前请点击右上角关注,天天 更新惊险刺激的历险故事!点击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故事!接待阅读,点赞,留言!
在半山坡的一处漫岗上,队员们手舞镰刀斧头在跟一头野猪坚持着。双方很是的主要 ,空气也像突然凝固了一样平常 。野猪哼哧哼哧的喘着粗气,嘴唇的吧唧声震天动地 ,离老远就听到了。从小在山里长大的人,对野猪是司空见惯的。别说是枪支在手,就是赤手空拳,我也没有恐慌过,着实 不行,爬树好了。尤其是群猪,别看是漫山遍野,阵容 浩荡,喊一嗓子,它们就会不战而逃。
可是,眼前的这头野猪,却照旧让我狠狠地吃了一惊。一样平常 野猪也就是二三百斤。除了有獠牙,嘴巴长,脑壳 大,耳朵小,跟一样平常 家猪是没有多大区此外。但眼前这头野猪却是非统一 般,黑褐色,毛眼闪亮,耳朵特小,显得很是机敏。尤其是它的眼睛,跟传说中的那头猪王一样,通红通红的,充满了杀机。体重有七八百斤,獠牙很小,紧护着上嘴唇。大嘴巴子山呼海啸般的吧唧着,白沬于也就一串串滴了下来。眼光 是敌视的,它居高临下,随时随地都市扑上来。我们只管 人多势众,却仍然是心惊肉跳 。挥舞看工具在两侧呐喊着。希奇 的是,二三十人困绕,它并不妄想 很快逃走,贪恋 的眼光 ,奋不顾身地死死盯着草丛中的谁人 偏向。四驴子是半个猎人岀身,有点儿胆子,顺着猪的眼光 里去,侧耳细听,突然惊喜的喊道:“妈的,怨不得它不走呢!小崽儿在这儿呢,你们听,吱吱叫呢!”说着,就走了已往,拨草一看,果真是一堆小野猪,刚要伸手,大猪像疯了一样,“忽!”地一下,就冲了已往。多亏四驴子履历 富厚,闪身一跳,才躲了已往。众人一阵主要 ,我也绝不迷糊 ,抬手就是一枪,“呼”子弹贴着野猪的耳边飞过,野猪一愣,大伙乘势舞着刀斧就冲了上去。一瞬间,我清晰地看到,野猪的眼光 是恼恨、贪恋 、绝望、悲痛的。我心田 发颤,端枪的手也不由的哆嗦了一下。野猪顺山坡冲了下去,我死后 的玉珍使劲抓着我的衣服,恐惧中叹息着说道:“妈呀!妈呀!吓死我啦!那猪的眼睛……好,好怕人哟!”我转头一看,她神色 苍白,吃力的支持 着,才没有昏已往。
野猪跑出了有七八十步,停在那儿,回过头来,顺着刚刚砍过的林带趟子,死死地盯着我们。
“带回去!把崽子带回去!”四驴子高声嚷着,“有崽子,它就得随着咱走。到帐篷前支两套子,妈的,跟老子拼命——”他脸冲下边的野猪叫道,“今天晚上,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吃你的肉,扒你的皮,喝你的血,掰下你的獠牙来。拿回家去给我儿子玩!”四驴子是个亡命徒,周遭十几个林场,一提四驴子三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一闹哄,大伙也就没心千活了。又是头一天,熟悉熟悉情形 ,于是我说:“下班吧,明天早点儿出工。”我们往回走,扭头一看,正像四驴子说得那样,那头老母猪,不远不近,在后面随着我们呢!
回到帐篷,四驴子先找了个竹筐把野猪崽盛了起来,又拿出一捆八号铁丝,用钳子,很快就做成了十几个野猪套。四驴子下套,是十拿九穏的,不管是狍子套、野猪套照旧兔子套。我参军以前,他还用套子套住了一头黑熊呢!
刚进屋,玉珍的父亲我的老泰山抗联老战士崔永焕就急了,吹胡子怒视 的,先用朝鲜话又用汉语,老羞成怒 般的高声吼道:“送回去!快送回去,活膩歪了呀你们!没事找事,这是闹着玩的嘛……”他神色 铁青,梗着脖子,额头上的青筋蹦得老高,像接触 一样,毫无探讨 的余地。
崔永昌和崔永焕,都是在朝鲜黄海南道的平泉郡岀生并长大的。1941年,被福丰稻田公司招雇而来到小兴安岭脚下萝北县。他们恨透了日本人,一来就加入了北满暂时 省委向导 下的抗联队伍,1947年剿匪,许多鄂伦春人受国民党的蒙骗,在佛山(今嘉荫)县加入了刘山东子(刘光财)的土匪队伍,即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混成第六骑兵旅。崔永焕等朝鲜青壮年在合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荆璞的率领下,生擒 了刘光财,一举端掉了沿江周围 的土匪窝子。剿匪中,岳父立了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岳父是革命元勋,也是声誉 武士 。他头上的光环许多,原来已经退休了,但这次行动,他的弟弟崔永昌,非让他亲哥哥来突击队当个照料不行。
老泰山来了,有点儿不太利便 ,尤其是和他女儿单独在一起的时间 。但他女儿却一百个赞成老父亲的亲征。路上,她就曾经跟我说过。我参军的第二年,她从学校放暑假回到了柳毛河,父亲一连三天没有回家。全场岀动寻找,最后在嘎拉旗河的沙滩上发现了他,其时,他已经昏厥不醒,岌岌可危 了。猎枪断了三截,身边齐刷刷的摆着七头野猪。而且都是这种红眼睛小耳朵的特种野猪。抬回家中,他半个多月,才逐步 地苏醒了过来。然后吿诉家人,那天黄昏他持双管猎枪,从石头庙子(野猪岭)翻山往家走。那一段路的山坡很陡,像悬崖绝壁一样。上面是峭立的石头,下边是滔滔的河水,小路很窄,仅能一人通过。他一踏上了这条险路,心里就感应恐惶不安。天又黑了下来,万一扑面 来了头野猪,躲又没处躲,藏又没处藏,那该怎么办呢?这儿的野猪,总有点儿神出鬼没的,看着是一只,眨眼就是一群。或者原来是一大群野猪,枪一响,就酿成了一只,一只特大号的孤猪。听说 大清帝国的祖始爷努尔哈赤登位那年,沙皇俄国派出一小股队伍妄想 偷袭黑龙江的将军衙门。乘桦皮舟过江后正酣然大睡呢。数千头红眼睛小耳朵野猪从山上扑了下来,悄悄地把江堤拱开,江水涌出,沙皇贼寇均被淹死。以后 以后,清朝帝国就在这群野猪繁衍的地方用石头修建了一座庙宇、庙中的塑像是一头野猪……时光流逝,沧海桑田,几经变迁,野猪岭下的石头庙子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我的老泰山崔永焕那天晚上在悬崖绝壁的小路上预感不妙,刚刚端枪在手,扑面 真就来了一头大孤猪,耳朵很小,眼睛通红,—身白毛闪着银光。他全身抖着,枪声一响,野猪咆哮的一声,像牛叫一样就从悬崖上栽了下去。他想快快逃走,没走两步,扑面 又来了一头。他用的是双筒猎枪,飞鹰牌子的,产地是齐齐哈尔。枪声响后,他急遽退出弹壳岑寂 岑寂 中重新压上了子弹。武士 身世的他,也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鬼呀神的一概不信。当他将第三头和第四头野猪击毙以后,他真就沉不住气了,全身哆嗦,大汗淋漓。第五头、第六头又上来了。他咬着牙关把子弹射了出去。打第七头时枪声刚刚一响,他两耳轰鸣,眼前漆黑,随着啊的一声,连枪带人就从悬崖上滚了下去妻子跟我说:“父亲太主要 了,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实着实 在的一群野猪,一头随着一头追上来无路可走。更不能退却,他前面的七只被毙命以后,父亲也栽了下去。后面的野猪,才顺顺遂 利的通过了这段险路。父亲醒来以后,立誓一辈子再不打野猪了。叔叔让他来当照料,也是来监视你们的。不让你们杀人如麻 ,松懈 了石头庙子的风水,这下明确 了吧!”
我明确 了也更糊涂了,传说是传说,传说取代不了现实。现实中,三五成群铺天盖地的野猪群又在哪儿呢?那头几千斤重的野猪王又在哪儿呢?
北方的夏日 夜短昼长。矇矇胧胧中,突然有人在高声喊道:“王场长!王场长!快点吧,欠好啦,野猪攻上来啦!”我一骨碌从铺上爬了起来,揉着眼睛一看,外面夜色已黑,林涛声呜呜地响着,那头野猪,为了救出孩子,果真最先 向我们进攻了。听声音,不是一只,而是多头。围着棚子,连拱带啃。工棚子是前些年采伐时扣的一座木刻楞。棚顶漏雨,我们把整个帐篷盖在了上面。周围 用石头压住,夏日 无大风,又不妄想 长住,一样平常 情形 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工棚子的一头是食堂,间壁墙是板夹泥的。旁边留了一个角门。食堂中尚有 一个套间,供伙食员专用。两位伙食员也都是鲜族女人,一位叫李春霞,一位叫金京子,包罗妻子崔玉珍,三位女性在套间的床铺上休息。我的铺头紧靠着食堂,第二铺就是老泰山。此时现在,三位女性也都爹呀妈呀的跑过来了,战战兢兢,像三只受了惊吓的小鹿。其他小伙子们也都手拿工具,严阵以待,很是的主要 。只有老岳父,只管 衣服没脱,躺在自己铺头上却是鼾声如雷的打着呼噜。
“妈呀!吓死我啦!吓死我啦!王场长,咋办呢?咋办呢?”金京子惊惶失措,哭叽叽的嚷道。李春霞倒很岑寂 :“怕啥呀,这么多人,野猪还能把你吞了不成。真是的,王场长这儿尚有 快枪。王场长,不行把枪给我,我也敢放。野猪再厉害,尚有 子弹厉害?”
小猪崽在竹筐中吱吱地叫唤。猪妈妈也就一头一头地撞门,门“匡咚”一声,“匡咚”一声。木门特厚,撞不开,就啃门框和门边的柱子:“咔嚓!咔嚓!”听上去很是的瘆人。“操!我让你没完没了!”说着,我把枪口探了出去,对着天空。“咚!咚!咚!”连开了三枪,枪声在夜幕下的群山中久久地回荡着。野猪阻止 了进攻,外面很快就清静 了下来。静的恐怖 ,只有林涛声,呜呜地响着。老岳父一个鲤鱼打挺,从铺上坐了起来,看不清心情,却是怒火冲天的:“谁让你开枪的?嗯?你他妈的不要命啦!”我关上了枪机,满不在乎的说道,“吓唬吓唬它们,这个折腾法,咱们还睡不睡觉了?”
“睡觉?你等着吧?”老泰山歇斯底里的拍打着床铺吼道,“睡觉,你等着吧!这儿是什么地方?知道不?不知道我告诉你,这儿是野猪岭,是石头庙子!……就你这一只破枪,就是给你挺机枪,你也得死在这儿!妈的,也太随便了,招呼不打,就随便的开枪,你的眼里,尚有 没有我这个照料?你以为我这个照料,是吃闲饭的吗?是来陪着你玩的?……等着吧,一会就有你悦目的!”他气喘吁吁,然后又指挥四驴子他们:“快!把蜡烛通通给我点上!出去几小我私人 ,把外面那堆木头赶忙给我点着!”
室内马上灯火通明。这条沟的交通很是未便,冬天运材汽车得翻一座山岗,而且照旧冻板路、成本高、不划算。因此,门前的楞场上就留下了两大垛小径木,足足有上百立方米。一旦燃烧起来,熊熊大火,足有几十米高,火舌舔着夜空,整个天下 都被映照的通明瓦亮……我有些心慌,更多的是恐惧,看看手表,已快十一点了。我打开对讲机,扯出了天线,把频道调好,就一遍又一遍的召唤了起来:“八洞六、八洞六!我是八洞四,我是八洞四,请回覆,请回覆!”崔场长的机子真就开着呢!联系上以后,我先汇报了这里的情況,然后又叨教 道:“崔场长!你说咋办呢?”对方半天无语,或许是在主要 地思索着吧,过了一刻钟,对讲机内就传来了崔场长斩钉截铁的回复:“那儿是个特殊的情形 ,怕发生意外,才给你派了个照料,我年迈 他履历 富厚,从抗联剿匪,他就时常在石头庙子一带运动。醒目 野猪的运动纪律,那头猪王,今天夜里,你一定 也能见到。王明贵,我郑重通知你,从现在最先 ,为了清静 起见,所有职员 ,一律听从老照料的指挥。若有违者,就地惩处!闻声 了嘛?”说完,那头就把机子关上了。看着火光,我手托对讲机,越发感应了冋题的严重性。
“把枪给我!”老泰山伸手把枪拿了已往,瞪着眼珠子,黄胡子一撅一撅,用从来没有的腔调,数落奚落 讥笑我道:“人模狗样的,不知天高地厚了!”枪在他手上,权力自然也就随之转移了,枪杆子内里 岀政权嘛!我被扫除 了武装,同时也就作废 了场长的权力。感应怨恨 、不平,同时也有点儿委屈。怨恨 的是,枪声一响,野猪没了。这是一种阴险 的预兆,像恶战前的清静 ,清静 得让人全身直起鸡皮疙瘩。我读过不少兵书,这也是一场鏖战前的自然纪律。毫无疑问,枪声一响,自身难以抗衡的野猪,为救崽子,回去搬援军 去了。
玉珍还在铺上跪着,一脸虔敬 ,双手合掌,捧在胸前。京子、春霞及不少男士也在呆呆地看着她,眼光 也是恳切而又虔敬 的。室内很是的清静 ,静得连相互的呼吸声都能听到。竹筐中的野猪崽子,也一言不发 ,像有预感似的在静默中期待着。外面火光闪动,并不时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在空中炸响。我知道:妻子是在祈祷,为了所有人的生命清静 ,为了开脱我的罪责而祈祷。由于 玉珍曾经多次跟我说过,父亲失事那天,母亲三天三夜都是跪在炕上祈祷的。
突然,从很是遥远的正北偏向传来了呜鸣的啼声 ,像闷雷,像海啸,像狂风,步步迫近,撼天撼地般的。与此同时,铺下竹筐内的小猪崽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是兴奋的、愉快的,也是兴灾乐祸的。四驴子被激怒了,咬着牙根骂道:“妈的!扔出去,烧死它们,让它们在这作妖!”
“你敢!”随着一声咆哮 ,老泰山的枪筒子一下就顶在了他的脑门子上,“再放肆,我先毙了你!”我扭头望去,只见四驴子螃蟹般的刀疤脸,蜡黄蜡黄的,目瞪口基,冷汗也从疤痕上一颗—颗地滚落了下来。现在,作为一家之主,我也意识到了,当初就不能听凭 四驴子的胡来,若不动它的崽子,老母猪是不会这么疯狂的。倘使我不开那一枪呢!四驴子惧于猪妈妈的威力,无人撑腰,也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猪崽子带回来的。是我一手制造了这场简直无法预料的灾难。
为了减轻负疚感,我想把野猪崽子送出去。这需要胆子,更需要勇气。犹豫再三,最终照旧放弃了这一念头。在事实眼前 我不得不认可,屋里所有的突击队员,包罗三位年轻女性,我的胆子最小,最虚伪,也是最大的一个怕死鬼。
两山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七八十米左右,中央 尚有 一条小溪在徐徐地流淌着。我们的工棚子在南山根下,属于阴面,这是违反了一样平常 建房知识的。首先是光照不足,尤其是冬天,屋子从早到晚都在大山的阴影下面。受情形 影响,人的精神也总是那么阴森 沉的。听说 采伐那年建这棚子就是老泰山来踩的点。其中玄妙似乎今天才有点儿隐约 约约的感受。首先是,夏日 多刮东南风,滔滔浓烟顺风向北吹去,呛眼睛刺鼻子。徐徐迫近的野猪群并没有像狂风吹落叶般的刮过来。只管 来勢凶猛,扑到跟前,又被滔滔浓烟和熊熊大火绝不客套 的阻挡在北山根下。火光徐徐熄灭,借着微光,我们都清清晰 楚的看到,烟雾中的灌木丛下面,数不清的红眼睛在一齐闪动着,像一盏盏的小灯笼,又似一股股的磷火、拆不时晃动燃烧着,叫人恐惧,恐惧得险些要窒息已往。
老泰山皱着眉头在室内走来走去。三十几小我私人 大气也不敢喘。我知道,野猪之多,洪水一样,一旦扑了过来,别说那钢刀般的獠牙,仅蹄子就能把我们踩成了烂泥!特殊 是那力大无限 的嘴巴子,那年冬天我带猎犬圈住了一头野猪,它见跑不掉,就背靠一棵大树坐下来以守为攻。猎犬呈扇子形围了上去。头狗大黑,体壮剽悍,从侧面想偷偷袭击,忽地扑了上去,说时迅那时快,只见孤猪大嘴巴子一晃,大黑“吱嗷”一声就被甩出去了二十多米远,只管 没死,也是全身瘫痪。放走孤猪,我把大黑背回了家中……看来今天夜里,凶多吉少。望着爱妻,我情绪 涌动,泪水也不知不觉的滚了下来。妻子还在祈祷,她面无人色 ,心情麻木,眼光 呆呆的,金京子和李春霞都在哭泣,是一种无声的哭泣,令人悲痛,令人心碎。
大火熄灭了,恐惧中传来了野猪群的哄啼声 ,拱土翻地的吭哧声,大嘴巴子的吧唧声,直到天亮,这种毛骨悚然的声响才悄悄地停了下来。
我们把所有的蜡烛点燃,尤其是窗台和门板下面,一根挨着一根的排成了—留儿。室内通明,蜡泪徐徐流淌,火苗悠悠晃动。
三点一刻,天色大亮,谁人 黎明,是在我们全体突击队员眼睛一眨不眨的盯视下,从黑漆黑 悄悄来到这个天下 上的。百鸟最先 了鸣唱,烟雾在氤氲中袅袅升起。望着如墨的山峦,和山峦上空如洗的蓝天,每小我私人 都不由的心情激动,激动的眼泪都快要流了下来。由于 人人心里都很是明确 ,殒命 的威胁已随着漆黑 而去。烛光还在燃烧,我清晰 地看到,帐篷的一圈都是燃尽了的朽木,蓝烟继续升腾,飘飘渺渺,透过蓝烟,无数的野猪在林子下面游动着。我终于发现了那头传说中的猪王,它蹲坐在地上,面临 着帐篷,足足的有一米半高,既老态龙钟又威风凛凛。两只前腿像两根毛茸茸的石柱子。油篓大的脑壳 在徐徐晃动着,眉毛雪白,像霜打过的干枯了的茅草。眼睛深深地潜在 在草丛后面,不见眼光 却叫人发瘆。特殊 是那一对獠牙,比镰刀把还粗,弯弯着,冷光四射。可以想象,只要它脑壳 轻轻一摇,再厉害的动物也会心惊胆战 。鼻孔像两只粗大的鼓风机,呼哧呼哧的喘息着,强盛 的气流,把朽木上的余火吹得一明一暗。“哎哟我的妈呀!这各人伙,简直就是一辆坦克车!真要扑过来,就咱这破屋子”拖沓 机手索二宝打了个寒战。四驴子急遽喊道:“快!快!快把崽子给它送出去!只要它们别过来!”在猪王的双方 尚有 几只特大号的野猪。像犀牛一样。这是一个家族,是生涯 在小兴安岭密林深处特殊的野猪家族。它们一色的小耳朵,红眼睛,啼声 似猪又像牛。
“哞——呕——”降低,粗犷,凄切而苍凉。时至今日,我通常 闭上眼睛,那头猪王的影子,就与嘉荫县出土的恐龙化石联系在了一起。
这是一群有数 、珍贵的野生动物。
是浓烟和猛火 阻止了它们前进的脚步。没有老泰山,没有这个老照料,昨天夜里,其效果 是真不堪想象啊!现在,老泰山手拎快枪,像战壕中的一位指挥员,仍然向远外视察着望着……他眼睛红了,仅仅一夜,满头的灰发已经变白了。
玉珍还跪在铺上一动不动。我感受到了心田 的疼痛,像撕裂般的疼痛。
太阳的笑容 终于从地平线上升了起来。老泰山转头扫了全体突击队员一眼,然后用嘹亮的声音吼道:“都出去,屋里一小我私人 不留,都跟我一块出去……四驴子,你把谁人 竹筐搬上,把孩子,交给它们的妈妈!”说着,一脚把门踢开,率先冲了出去。
我把爱妻扶了起来,她的手脚竟是冰凉冰凉的,脑壳 依偎在我的胸前,憔悴的面容仍不见血色。玉珍呵玉珍,你的精神肩负太重了。此外家庭都是一小我私人 在此,而我们呢?一旦有个闪失,就是全家覆灭了。
以烟雾为屏障,以溪流为疆界。全体队员在屋子前面一字排开,手拿斧头镰刀,目视着烟雾那里 的“八戒”学生 。待我挽玉珍出来一看,门口所有土地 通通都给野猪翻了一遍。黑土上飘散着猪毛,空气中弥漫着刺鼻子的腥臊味。四驴子算是有胆子的,手捧竹筐,把小猪崽轻轻的倒在了地上。没等转头,那头老母猪就忽地一声冲了过来,舔舔这只闻闻那只,那份亲密那份疼爱,连高智商的人类都深感自愧不如。母猪用嘴把崽子一只只叼走,没出去十步远,就“噗通”一声躺在那儿,四腿长伸,让孩子吃起奶来。无忌无虑,幸福清静 。
老母猪在喂奶,猪王及子孙们仍然是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似乎在耐心的期待着烟火的熄灭!好一声令下,冲上前来。现在,我的岳父崔永焕出马了,他气宇昂然,一身正气,一手握枪,跨前了两步,对着阵中的猪王,言辞恳切、情绪 深沉的高声说道:“老人家,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来是从事生产,搞成林解放,不是来争取 土地称雄决战 的。您看明确 了吧!昨天的事,是孩子们出于好奇,跟你的晚辈开了个玩笑。既无伤亡也没流血,您台端惠临,亲自出征,到底是为了啥呀?是记前仇,怨怨相报?照旧看看我的枪法,跟昔日有没有逊色?我崔永焕不愿意伤你,可也得让你看个清晰 ,省得 忏悔而折了你的寿命!”说着,右臂猛的一甩,枪口冲天:“砰”的一声,一只松鸡一头从空中栽了下来,不远不近,不左不右,恰恰栽在了猪王的眼前 。“好!太棒了!崔师傅,宝刀不老,风范不减昔时 啊!”“哎哟!不愧是崔炮手!昔时 剿匪,刘山东子,在半里地之外,就被他从马上打了下来!”人们情绪激昂议论纷纷。我心里猛地一颤。作为三军 的特等射手,与岳父相比,功夫武艺真是天壤之别,自愧不如了。我为岳父自豪,也为自己的虚伪而忸怩 。我舒了一口长气,再看扑面 ,猪王对死鸟置若罔闻,倒是死后 几只大猪崽子冲了过来,你抢我夺,松鸡被其中的一只衔住,脑壳 一扬,就吞了下去。猪王站起来了,四腿迈动,我清晰 地看到,它不是雄性的大跑卵子(雄性野猪),而是雌性的一头老母猪。松懈 的奶子蹭地,步履蹒跚,俨然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太太啦!
这是一个母系社会,在兴安岭的大山深处,繁衍栖息着她重大 的一个野猪家族。早在七世纪初,渤海王国的靺鞨族就有象形文字纪录,雌性野猪是群体生涯 ,而雄性的则是孤猪。它们运动规模很广,从外兴安岭的庙屯、库页岛,到黑龙江流域的开库康、十八站,一直到长白山北段的老爷岭上,都曾看到过这种野猪的影子。这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其大脑的发育水平,跟海豚、猴子、猩猩、大象差不多。伪满时期的《卜奎日报》曾先容 过这种野猪的生涯 习性:阴险狡诈 、刀枪不入、喜袭击外国人。尤其北满林区的日本关东军。昔时 驻在那一带的北安联队长本田肆郎大佐就曾恶狠狠地骂道:“赵尚志的、冯仲云的、野猪的一样、死了死了的!”不知何以,也许像其它珍稀野生动物一样吧,这种野猪的运动规模越来越小。到“文革”后期,仅能在烟简山、老白山、金顶山、汉冲沟山、摩天岭周围 才气看到了。这些山头都在鹤北林业局的统领之内,而鹤北局,则是共和国最年轻的一家森工企业。大面积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不仅仅野猪,而且也是棕熊黑熊东北虎款子 豹的存身之处和生涯 乐园。九十年月 初期,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节目组专门来了一趟,也曾到柳毛河林场做了专访。遗憾的是,别说整个野猪家族的重大 群体,连一只红眼睛小耳朵的野猪都没有见到。八十年月 中期,在野猪岭下,这个家族的整体 泛起,在这个天下 上,也许是最为壮观完善 的一次了吧!果真云云 的话,其时的眼见 人,应该是最大的幸运者。这一次我们也成了幸运者,岳父鸣枪击鸟以后,猪王徐徐而动,而前后左右的保驾护航者,都是清一色的雄性大跑卵!
猪王在视察着我们,危险并没有消除。适才岳父讲了:“我们不是来争取 土地的……”我心里倏地一亮,下令 索二宝:“发念头 车,马上返回!”再不返回,就只能是错上加错了。脱离 石头庙子、猪群自然就会散去。
在机车旁边,二宝子突然失声喊道:“王场长!你快来呀!”我闻声赶去。低头一看,是四驴子拧的那些野猪套子,均被野猪衔到了这儿,然后用牙齿一节节的咬断了。长如筷子,短似洋火,想想昨天晚上嘎叭嘎叭的响声,再看看这些筷子粗细的铁丝线,望着扑面 的猪群,我再次的感应头皮发炸,后背发凉,根根汗毛都直竖了起来...
人都说虎牙尖,狼牙快,豹子牙齿没得赛。而野猪牙.. .想着,我敦促二宝:“发动车,快走!快走!这帮家伙,简直就是一群妖怪 。”拖沓 机发动了,启机的声音尖锐高昂响亮,在大山的底谷,像一头猛兽的嚎啼声 在回荡着。猪群毛了,乱蹿乱叫。猪王昂起头来,用恐慌 的眼光 望望我们再看看机车。这个怪物,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势 吧!它晃动着脑壳 ,倒创着鬃毛,嘴巴子杵地上:“阵!”的一声吼叫,像拉满了弓的一只快箭,随时随地都能射来。我不由一阵主要 ,随手抓起了一把六磅大锤,握在手上,摆好了决战的架式。队员们拉开了距离,老泰山把准星定在了野猪王的眼睛上。 金京子“妈呀!”一声惊叫。机车的柴油机最先 了正常运转。我对三位女性高声喊道:"玉珍、京子、春霞,快进机车内里 去!"她们迅速的钻了进去。拉上铁门,我舒了一口长气。二宝子来了性情 ,也许是为了转移野猪们的进攻目的 ,减轻我们的精神压力,把油门一按到底,挂上了五挡,咬紧牙关掌握着使用 杆,拖沓 机突突突地吼叫着,所向披靡 横冲直撞,履带扬起了木灰,像一头发狂了的猛兽,奔猪王就扑了已往。人们乐了,高声喊道:“二宝子!往死里轧,轧死它们!”
“对,轧死这些家伙吃肉,看它们再凶!”
岳父却勉力 劝阻:“二宝子!二宝子!不能危险 它们啊!它们是无辜的哪!又没危险 咱们!”我也帮着岳父喊道:“二宝子,别轧!别轧!”可是已经晚了,猪窝像炸了营,东蹿西跳,峰眸地叫着。山林下面像突然被插了马蜂窝。猪王别看平时行动妙缓,步履蹒跚,要害时刻照旧很是机敏而又迅速 的。它“哞!”一声怪叫,身体—晃贴着链轨板就躲了已往。倒是随后一头大公猪,躲闪不及,拖沓 机一颠,就从它身上轧了已往,马上皮开肉绽,脑浆迸裂一命呜呼。野猪们贴着山根上蹿,二宝子迅速又把车头调了过来,三百六十度的急转弯,油门不减,继续再追。
猪群拥着猪王,狼狈逃窜,像一阵飓风,眨眼之时,就消逝 得无影无踪了。
从黎明前的三点,到天亮后的五点。相持了两个小时,对手看上去势不行挡,但决战 中仅一台拖沓 机出马,重大 的野猪群就彻底土崩瓦解了。望着猪群消逝 的偏向,我征求各人的意见:“咱们继续干呢,照旧回家?”大伙儿说:“回家!回家!”四驴子第一个亮相:“这一宿,他奶奶的,差一点没把人折腾死,还干呢!谁愿意干谁干,我是一会也不能在这呆了!我死了没关系,早晚都得死,这几个老娘们呢!那不是白瞎了嘛!”
“往回走吧!这是持久战,啥活也不是一天干的!”老泰山以照料的身份也表了态,“这是成林解放,又不是造林,一年就那么几天。不能误了季节。幼林扶育,成林解放,啥时间 干不行....强扭的瓜不甜,大伙都散心了,再干,也不会有好效果 的。再说这帮猪再回来,可真就是玩命喽!”众人的意志,我这个新任场长也欠好委屈 !我再次与崔场长通了话。“回来吧!回来吧!平安无事,比啥都好!生产的事,以后咱们再说!”通过对讲机,场长在那头高声敦促道。
我们返回了,一个更大的陷井也在等着我们。这是在场的人谁都没有预推测 的,包罗我的岳父老泰山。事实也再次向众人 证实 ,这个野猪家族的智商和头脑 能力,与人类相比,不仅不低,从某个角度说,而是更胜一筹。
返回的路上,拖沓 机突突突的响着,大木爬犁上多了一头死野猪,七八百斤重。下战书 抵家,各家各户就能改善一次生涯 了。爬犁太小我们只好徒步而行,被拖沓 机远远的拉下了有二三里地。在嘎拉旗河岸边与黄龙沟的交汇处,拐过山包,我们远远的看到,拖沓 机陷住了。突突地响着,只管 拼命挣扎,可就是寸步难行。拖沓 机陷住,在山里一样平常 情形 下是很少见到的。况且现在也不是季节,六月初,草甸子下面,还没有化透,山里人都知道,阴坡处的草甸子,属永冻层,直到老秋,也化不透的。拖沓 机怎么会陷住了呢?
黄龙沟离场部约莫有三十多里地,山上多跳石塘和石砬子。山坡较陡,树木都不多,而且多是老头树,稀稀拉拉,成材的没有几棵。可这条沟的蛇特多。当地人叫它长虫,最大的两米多长,锄把粗细金黄色,爬行的速率 极快。个此外有毒,扭成一个蛋,时常就从山顶滚了下来,带着风声,让人生发怵。鹰隼狐狸较多。因此没有鼠害,此沟最顺应 栽植樟子松。但一再 发动由于 怕蛇职工们谁也不愿去那里植树。拖沓 机在这条沟口上陷住,我心里自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四驴子说:“奶奶个熊的,是不是长虫在那儿生事 呢!打走野猪,迎来了黄龙,今个,可就有戏唱了!”
一到近前,我们就围了上去。三位女士已经从驾驶室钻了出来,满腹忧虑,一脸的哭相。特殊 是金京子,没到跟前,就咋呼上了:“场长啊!快来吧!这些死野猪,跟咱们没完啦!你瞅瞅!你瞅瞅”我一看,从山根到河滨约莫有二十多米的距离,均被野猪拱出了一条四米宽的带子,土壤 翻了上来,散发着黑土的芬芳。土壤 中尚有 猪毛猪粪和污水。毫无疑冋,拖沓 机无路可绕了,必须横穿而过。问题是,下面是冻板,化层不到二尺,链轨抓着冻底,稀泥再深也陷不住呀!同时我也感应惊讶,一是野猪绕在我们前面设置了这道障碍。二是仅仅两个小时,这么大的面积就被翻了一遍?要知道,甸子中的草根特厚,有些地段用拓荒 犁,一两次都很难切开。这些野猪,真他妈的神了!
玉珍拽了我一把,不无关切地说道:“明贵!这次可不能胡来了呀,你看看河套内里 !”我扭头看去,大河两岸均是枝条悠悠的红毛柳子,密密匝匝,风雨不透。而且青草半米多深了,除了水声,能有什么了。但我信托 ,玉珍心细,没有异物,是不会提醒我的,同时我也注重 到了,顺着野猪翻过的地方,河水很快就漫延了过来,眨眼之时,就到了跟前。河床低于岸边,晴空万里,上游又没有山洪暴发,希奇 ,河水怎么会倒灌而来呢?神了,真他妈的神了!二宝子一身泥水和油污,苦着脸说:“王场长!你说咋办呢?底盘托住了,前后都转动不得了!”
我仔细看了看,链轨已经陷到了稀泥之中。是后面的木爬犁造成了阻力。链轨磨擦着冻层、冻层融化,就形成了泥浆。直到后桥及机体被烂泥托住。河水到了跟前,涌入车身下面,而且还在继续着。我来不及多想,付托二宝子:“把销子摘下来,大伙一齐推,看能不能出去?”二宝急遽摘下了三角架,爬犁跟车头彻底脱钩了。然后钻进驾驶室,大伙一齐围上,无奈拖沓 机不是汽车,履带旋转着,靠不上人,使不上劲。再说了,这块铁疙瘩,自身就是一万来斤,陷在泥中,仅靠三五小我私人 ,又能怎么样呢?“屁事不妥!屁事不妥!”四驴子溅了一身污泥。河水继续增多,失去了木爬犁的牵引,车头越陷越深。徐徐地,链轨不见,机械泡在黄泥中,发念头 却仍然有节奏的响着:“突突突!突突突……”见事欠好,二宝子紧忙跳了下来,没有摘挡,空负荷,履带在一直 的旋转着。机身也一点点地陷下去。机车越陷,我心里头越沉。要知道,柳毛河林场不是富足单元,这合拖沓 机是夏日 生产中唯一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我是生产场长,失去了拖沓 机,以后 生产怎么办呢?
李春霞眼尖,突然恐慌 地喊道:“哎哟妈呀!你们看哪!水里头是什么?”大伙清清晰 楚看到,泥水先是黑的,随着链轨的一直 旋转,泥水就由黑褐色変成了橙黄色、灰白色,发念头 还在给续突突。洛阳拖沓 机厂的发念头 ,其质量可以说是天下 一流的。机体陷下去了一半,险些就要浸泡到了排气管于和空气滤清器。坐席早已不见,使用 杆仅仅能露着两个手柄,发念头 还在不紧不慢嗵嗵地响着。同时大伙也惊讶地发现,有几条灰黄色的长虫在徐徐地游动着。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污泥酿成了古铜色,随着一阵刺鼻子的腥膻味,霎那间,几百条长蛇就一齐从水下钻了出来,迎着阳光,昂看脑壳 ,眼睛贼亮贼亮。也许是不顺应 地面上的温度吧,身体有些发僵,但嘴里的信子却是在飞快转动着这么多的黄蛇一齐泛起,人人恐惧得目瞪口呆,汗毛直竖。“哎哟妈呀!吓死我了!吓死我啦!”金京子手忙脚乱 的喊着,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众人后面。
“玉珍姐!快走呀!快走呀!”李春霞神色 蜡黄,全身筛糠般的发抖着,哭叫道,“我的腿,腿,不听使唤了呀!玉珍姐,快走!快走啊!”
妻子崔玉珍,紧迫 关头却显得很是的岑寂 岑寂 ,她拉着春霞和京子的手,轻轻说道:“不怕的!不怕的!它们刚刚蛰伏醒来,行动不快,是追不上人的!”玉珍一说,毛骨悚然的我,也在惴惴不安中岑寂 了下来。退却了几步,继续关注这些冷血动物的进一步行动。这些黄蛇最大的有两米多长,胳膊粗细,由那条大蛇率领,蛇群并没有随处乱爬、似乎是在一种无形的体现指导下,逐步 爬上了木爬犁。继续前进,最后爬到了那头殒命 了的野猪身上。数百条蛇,眨眼之时就把野猪的遗体 覆住了。在温暖的阳光下面,水中钻岀来的蛇,还在继续运动着不大一会,在野猪的遗体 上面,是非粗细纷歧的黄蛇,堆起来足足的有一尺多厚。
发念头 终于阻止 了运转。水面上,仅仅露出了排气管子。霎那间,周围的一切也都变得那么悄然 。我往前走了十几步,从红毛柳条子的误差 中望去:河里的景观,又一次的让我惊讶不已。
河水中有几十头野猪,身体靠着身体,像人类中的抗洪勇士,用自己的躯体,建成了一道水坝,树起了一道猪墙。墙这边水高成湖,逼水淌了过来,把机车淹没。望着它们,我全身上下不由打了一个透骨的寒颤。
我们继续徒步前进约莫走出了一百多米,玉珍再次提醒我道:“明贵!你看看后面!”我扭头一看,全体突击队员在磕磕绊绊的跋涉着,后面是老岳父,身背长枪,目无心情。“你往山顶看呀!”妻子头也没回。
我停下来,转过身望去,在黄龙沟北坡的山顶上,野猪王在一动不动的盯着我们呢!仰面 屹立 ,威风八面。长长的獠牙很是耀眼,雪白的眉毛更是格外明确 ,死后 和左右是它大巨细小数百个子孙,下沉了的拖沓 机就在它的铁蹄下面,真要是袭击我们,我们就是插上同党 也休想逃走 啊!
我心里又是一沉,毫无疑问,当初二宝子不开车轧死那头野猪,拖沓 机是不会陷在那儿的!它们这次行动,是针对着这台东方红牌拖沓 机来的。动物的抨击心很强。仰面 再看,那几十头野猪从河套中爬了上来,全身水淋淋的。正一个随着一个,嘴上哼哼着,一步步爬上了山去。不知是哪根神经的支配,冲着猪王,我铺开 喉咙的喊了一嗓子:“猪王,再见了”受我情绪的熏染,众人也都停了下来,没人指挥,却是一片同声的:“猪王!再见了!放心吧,我们人类,会善待你们的!”
岳父老泰山再次鸣枪,以示礼谢,“咚!咚!咚!”
人类的友好信号,猪王和它的家族也许是吸收 到了吧!先是猪王一声吼叫:“哞”苍凉、悲切、辛酸 。继而是数百头野猪一齐“哞——呕——!哞”鸣叫!
完!
谢谢阅读主页有更多惊险故事,接待关注,留言,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