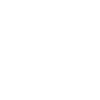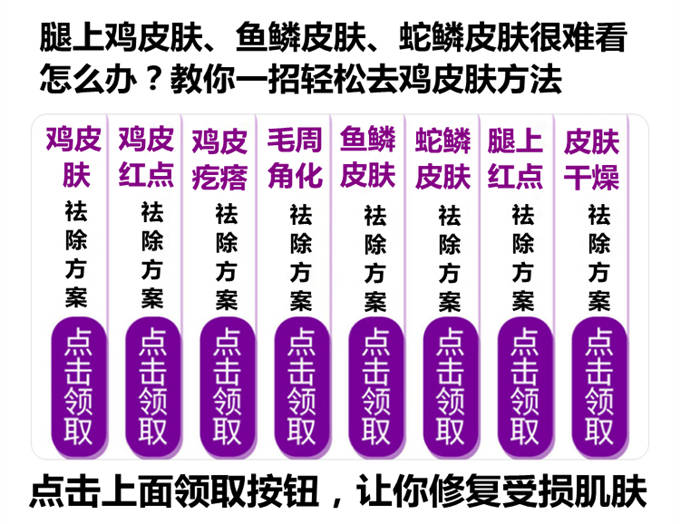作者:亦凡
我们村有几户姓令狐的人家,据老人们说,他们是早年间从外地狩猎来的。昔时 他们的祖先 来到我们凤凰山一带,看到这里风物秀丽,野物许多,就定居下来以捕猎为生。
到了令狐野这一辈九世单传,已进入相助社时期了。令狐野家里穷得丁当响,好不容易娶了个半痴的婆娘,传宗接代。也许老天不想绝令狐这一门,完婚 不久他婆娘就生个了儿子,令狐野很是兴奋,给他的儿子取名令狐欢。
狐爷和獾叔是人们给他爷俩起的外号。这尚有 个泉源 。令狐野年轻那会儿,个子不高,黑黝黝的皮肤,体格结实,只有一点很特殊,就是那张狐狸相的脸,黄黄的长长头发,遮掩 着的吊吊的两只眼睛,两只倒三角的耳朵,斜挂在脸双方 ,尖尖的嘴巴,时不常露出一口大黄牙。老人们不能叫他野(爷),叫令狐又拗口,于是就叫他小狐。叫惯了,令狐没人叫了。小字辈也随着叫狐爷了。等狐爷上了岁数,留起希罕 的胡子,就越发像狐爷了。
獾叔这个外号,倒不是他长得像獾,最先 是由于 “欢”与“獾”谐音。厥后,狐爷说了个故事,才叫了起来。
约莫在獾叔四五岁的时间 ,有一年炎天 的晚上,狐爷吃醉了酒,在村里一棵大槐树下和几个邻人 纳凉,旁边燃着蒲棒驱赶蚊子,烟袋锅一明一暗,人们有一问没一答地说着家常话。
这时,一个叫栓住的冒了一句:“我说狐兄啊,一直有个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啊?栓住兄弟。”狐爷说。
栓住道:“我发现自从你有了小欢后,怎么不狩猎了呢?你那枪该生锈了吧,祖传的本事也快丢了吧?”
狐爷叹了口吻 ,“说来话长了,算起来,我们家到小欢已十世单传了。昔时 我爹娶了我娘,五六年怀不上孩子,我爷爷嫌疑 ,我们家人丁不忘,是不是与猎杀有关系,以后 我们照旧洗手不干了吧。
中央 我爹停了一两年,效果 很快生了我,大伙都知道我娘却在我不到一岁时死了。我又成了九世单传。”
这时,旁边一个叫狗蛋的小孩急了,“狐爷,说你的事,说你爷爷和你爹作什么。”
狐爷笑了声,“毛草鬼,让我喘口吻 。”接着说,“就在生小欢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我去山里埋地枪,准备捕杀一只经常出没的野獾。等忙活完了,正要起身走,突然一阵眩晕,眼前一片漆黑。等我定过神来,我发现周围大雾弥漫,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正着急突然发现在不远处一个偏向,隐约有灯光,我顺着灼烁走了约一个时间 ,终于望见 一座茅屋。
我上前推开柴门,只见一个老者正在院里打坐。这老者身穿宽大的粗平民 衫,脚蹬麻布芒鞋,鹤发童颜,吐气如丝,入定神闲。听到我的新闻 ,双目逐步 张开,马上两道炯炯眼光 ,令我毛骨悚然 。”
狗蛋又抢了一句,“你准是遇到鬼打墙了!”
狐爷说,“这时谁人 老者发话了,声如洪钟,发自丹田。”
老者问,“年轻人呀,看你的穿着,准是个猎户,是不是迷路了?”
我对答,“是啊,原来我经常来这里,怎么没见过您老呢?”
老者笑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扑面 不相识啊。来,先喝一口我自己泡制的茶。”
狐爷端起一只粗拙的茶碗,感应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喝了一小口,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直入心脾,不由地赞了声“好茶!”
这时,老者又发话了,“茶要品,话也要品呀。不是有句话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年岁 轻轻作猎户,要给子孙多积些德啊。”
我这时,猛一仰面 ,老者和茅屋都不见了,我手上正端着自带的水壶,还冒着热气。雾也散了,发现离回家的路偏了十几里地。
栓住说,“狐兄啊,你准是遇见狐仙了!”
狐爷又深深地吸了口吻 ,不作声了。
狗蛋又急了,“这就是你不狩猎的理由呀。为什么呢?”
狐爷摸了摸狗蛋的头,又说道,“我恍模糊惚回到了家,倒头就睡。模模糊糊 中,谁人 老者又泛起了。他告诉我,他是在泰山修炼多年的狐仙,已经五百多岁了。认得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你们之以是 人丁不忘,就是孽债太多,你要将血脉传下去,必须以后 不再狩猎,他保证向泰山老奶奶给你求个儿子。我正兴奋,他喏了一声,这是你的儿子。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野獾,正呲牙咧嘴地向我扑来。我一身冷汗,似梦非梦。”
狗蛋也吓了一跳,名顿开,“噢,原来我欢叔是只獾托生的呀!”
人们哈哈大笑,散了睡觉去了。
以后 ,獾叔的外号叫的更响了。
有些事情是不能体现的。狐爷有了儿子之后,以后 不再狩猎。对狐狸也崇敬起来,以至于将原来打来的狐狸皮,也供了起来。
邻人 张奶奶笑话他,“狐兄弟,狐狸是你祖宗啊!”
狐爷笑了笑说:“他也是你祖宗啊!”
这两小我私人 的对话,在厥后还真有段故事呢。
话说回来,农村的孩子,像草一样,见风就长,“欢”成了“獾”,撒着欢疯长。不外我獾叔的疯长,也真有些獾的习性。
獾这种动物,似猪又像狗。在我们那里有时分不清是野猪照旧野獾。獾嗅觉迅速 ,好掘土,居穴。一样平常 住野外的宅兆里,以至于我们都想杀之尔后快。可是 它很狡诈 ,昼伏夜出,喜欢独居生涯 ,而且几天就换一个住的地方。獾的食性很杂,植物的根茎、玉米、花生、菜类、瓜类、豆类通吃,昆虫、蚯蚓、田鸡 、鼠类和其他小哺乳类、小爬行类,它也喜欢。由于 这个缘故,在我影象里,似乎我出来事情十多年,回家去还听说,獾糟蹋了几多几多庄稼。
对照一下,獾叔的习性真是这样的。忘了先容 了,我和獾叔是同龄人,只不外他萝卜不大,长在辈(坝)上。下面说说我们孩童的事,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名副着实 獾的习性了。
到了我们十二三岁的时间 ,已经是人民公社生产队时期了。我们那时上学基本是玩,识的几个字而已。辽阔的野外 是我们的大课堂,一年四序 都在疯跑。
獾叔自然是我们的孩子王。
炎天 ,打瓜围是我们最刺激的一场游戏。既好玩,又实惠。其时,生产队的瓜园是最诱人的,长着黄瓜,梢瓜,甜瓜,小同伴们垂涎三尺,时不常就去打个瓜围。
獾叔既是总指挥,又是战斗员。
一天晚上,月亮升起来了。我们来到二队的瓜园。这个瓜园,我们最熟悉,东边临着一条宽水沟,西边和北边靠着庄稼地,南方 紧临大道。看瓜园的王老头,很倔很认真 。最恐怖 的是那条大黑狗,不知什么时间 就窜出来咬一口。性急的狗蛋,一纵身就要往瓜田里钻。獾叔一把扯住他,低声骂了句:“操蛋玩艺儿,想让狗咬啊!别急,现在月亮光光,人和狗都精神,等到后三更 下手 。”
沉了一会儿,他又说,“下手 时,狗蛋你去搪塞那条黑狗,在靠庄稼地那双方 弄出点新闻 ,把狗吸引已往。万万 别让它咬着。”
又指着二娃和我说,“你们俩在南方 道上唱歌,把王老头吸引已往。其他事你们就不要管了,等着吃瓜吧。”
獾叔“嘿嘿”的笑了,露出一口大黄牙。
到了下三更 ,月亮偏西,夜深人静,我们下手 了。狗蛋把狗逗的嗷嗷叫,我和二娃在大道上唱歌,把王老头吵醒了。他披着衣裳对我们说,“熊孩子,快回家困觉去吧,别打瓜的主意,小心让狗咬你。”我们说,“王大爷,我们才不吃你那破梢瓜呢,我们在演奇袭白虎团来!”
这时,我们从侧面看到,獾叔从东面沟里一蹿就进了瓜田。只见他紧贴地面,匍匐前行,听得瓜蔓窸窸窣窣,很像一只獾在拱瓜田。
过了约莫一袋烟的时光,听到獾叔高喊“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我们知道已经得手,阻止 了佯攻,到事先约好的小河滨的树林汇合。
等见了獾叔,我们都笑了。只见他全身 上下全是泥,头发上还沾着瓜叶,活脱脱的一只大獾。
地上摆着各色的瓜。我们到河里一洗,就大吃起来。獾叔吃的特快,他的大黄牙,发出“咯哧咯哧”的响声,真像獾咬吃工具的声音。
我们吃的肚子溜圆,就唱着歌回家了。
秋天,在那些经常吃不饱肚子的年头,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
在秋天,野外 不仅五彩斑斓,而且随处是可以吃的工具。玉米结下牛角般的棒槌,大豆摇起悦耳 的串铃,地瓜拱破土垄,裂了好大的纹。枣树、梨树、苹果树,都结满了果实。这时,学校也放秋假了。獾叔和我们欢喜的秋天来了。
那时间 ,生产队里活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要加入劳动,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好比拔豆子,掰棒子,刨地瓜,等等。我们最愿意拔豆子,可以烧崩豆吃。虽然这不能让大人望见 。
一次,獾叔和我们几个孩子去拔豆子,队长让獾叔带队,就不委派大人了,但必须保证一上午拔完那两亩地。我们谁人 兴奋啊。
獾叔说:“看把你们兴奋的。队长让我带队,各人都要好好干,上午必须干完。”说完,就蹲下身呼哧呼哧地拔起来,我们紧随厥后 ,也拔起来。我实力 小,落在后面。看到獾叔穿着一身黑衣服,又低着头,一直往前拱,真像一只獾啊。
快到中午,我们终于拔完了豆子。大伙累得躺在了地上。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獾叔,咱们烧崩豆吧?”于是,各人都雀呼起来。
“好,犒劳一下各人。”獾叔说着抱起一捆豆子,向河崖跑去。只见他点着了豆子,脱下褂子迅速扇着,让烟灰迅速扩散,不至于让大人发现。等火灭了,地上落满了金黄的崩豆。我们抢着吃起来,纷歧会儿,一扫而光。突然,我们相互看着笑起来,每小我私人 都灰头乌嘴。大伙纷纷跑到河滨去洗脸喝水。我发现獾叔洗脸喝水与众差异。他把脸浸到水里,摇晃着头,一会儿就洗净了,然后伸出舌头像动物一样添水。喝完了,又摇晃一下头。看到这些,我越发信托 獾叔是獾托生的了。
獾叔尚有 些像獾的习性,他特喜欢钻岩穴 。有一次,我们在一块玩,他说,“我们到石灰窑上去烤地瓜,烧玉米吃吧?”我准备去地里刨,他说,“跟我来!”他带我们来到一个窟窿,哎呀,洞里啥都有啊。我们取了地瓜、玉米,花生,到石灰窑上,美餐一顿。
獾叔胆子特殊 大,自己可以在坟茔地里待上一晚上。有一次,捉迷藏,周围 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他。厥后,他说,在一个挖空的宅兆里头,睡着了。
獾叔的这些习性,不知是天性,照旧无意 ,造成了他厥后的悲剧。
在獾叔十六岁的那年秋天,狐爷家发生了灾难性剧变。
自从人民公社以来,猎户都被捆在种地,农业学大寨上。种种野物快速滋生 起来。泛起了野兔满山跑,野猪野獾随处拱的情形 。
我亲历了一件趣事。傍近过年的一个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听到父亲喊我,“快起来啊,逮兔子啊!”我一骨碌爬起来,穿上衣服就蹿到院子里,问:“兔子在哪儿?”父亲指了指草垛,我心心相印 ,抄起扫把,围住草垛的一个洞口。当兔子试图逃跑时,被我一扫把,父亲一扫把,打在地上。好大好肥的一只兔子,真是搂草打兔子,捎带办了年货,过了一个好年啊。
着实 ,野兔的大量滋生 ,对庄稼损害并不大。而野猪野獾乱拱乱吃,严重破损 了庄稼,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于是,祛除 野猪野獾成了一项紧迫使命 。
生产队里开会,部署逮杀野猪野獾事情。还给予奖励,每逮杀一头野猪野獾,计二百个工分。还特殊 勉励,狐爷这些老猎户要起劲 带头。
会开完了,狐爷犯了嘀咕,做与不做成了问题,纠结的吃欠好睡欠好。他想,自从听了狐仙的指点,不仅有了儿子,而且很是平安。若是 开了杀戒,神灵怪罪下来怎么办?不做吧,生产队又有要求,确实那些野猪野獾也在作孽。正在狐爷犹豫之际,他谁人 半痴的婆娘语言 了,“你不是有支地枪吗,你把它埋上,野猪野獾自己踩上,说明它活该,又不是你亲手杀的。”
狐爷一拍大腿,笑骂:“你这个傻娘们,今天还还真是赛诸葛了!”
狐爷决议 用这种方式加入猎杀行动了。
狐爷一旦作出决议 ,就最先 做准备。当天晚上,从木箱子拿出那支地枪,擦拭起来。
灯光下看那枪,是一根约一米长,直径五公分的铜管,管上有些孔,管的一头堵着,另一头有一个机关,连着撞针。将火药混上砂子,用一根绳子拉起撞针,埋在地下。一旦猎物踩上或绊上绳子,撞击引爆,这根管子便旋转着飞起来,砂子便扫射起来。由于地枪发射的是个扇面,猎物一旦碰上,非死即重伤。数不清有几多猎物,倒在这枪口之下。
这天,狐爷在擦枪时,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感应枪冷冷的。他重新擦上黄油,用布裹上,放了起来,想沉些日子再说。现实 上,对一个洗手多年的猎手来说,照旧有一个结没解开。
过了几天,村里一个猎户逮了一头野猪,奖了两百个工分。狐爷便下定了刻意 。
那天晚上,金黄的月亮挂在中天,黑幽幽的山谷,显得异常神秘。狐爷将枪埋在一个岩穴 口,这儿离野獾糟蹋庄稼最多的玉米地不远。野獾经常出没,狐爷埋好枪就回家了。只等明天来收猎物。
一连过了四天,没有新闻 。狐爷并不着急,由于 他这次原来就是无邪 烂漫 的。
到了第五天晚上,狐爷去看了一遍,就回家来了。他突然感应乏的慌,就上炕睡了。朦胧之中,谁人 狐仙老者又来到他眼前 。这次他不再平易近人 ,而是怒目相对,斥骂道,“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忠言 ,又要大开杀戒?”说着又向后一招手,一头野獾呲牙咧嘴,迎面冲来。狐爷“啊”了一声,惊醒了。
狐爷坐了一会儿,心照旧怦怦直跳。于是,披上衣服又向埋枪的地方走去。
狐爷走在去野外 的路上,天色已是后三更 了。万籁俱寂,凉凉的秋风,吹的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就在快要到埋枪的所在了,他突然听到玉米地里“唰啦唰啦”一个劲的响,纷歧会儿蹿出一个黑影,急急地向岩穴 跑去。狐爷的心一下子跳到嗓子眼儿,只听霹雳 一声,地枪响了。谁人 黑影惨叫一声,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狐爷疯跑上去,借着月光一看,“啊”了一声,一下子也倒在地上。
等狐爷醒了的时间 ,他儿子欢,我獾叔公的遗体 也入敛了。狐爷嚎了一声,“作孽啊!”又昏了已往了。
獾叔由于 好钻岩穴 的习性,踩了狐爷的枪。现在,带着全身 的砂子,真钻岩穴 去了。
埋葬了獾叔,狐爷一下子老了,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五十多岁了。他那半痴的婆娘也彻底疯了,不久就不知疯到哪儿去了。
儿子死了,婆娘没了,狐爷一把火烧了供的狐狸皮,彻底开了杀戒。他整天扛着枪,见什么野物就打什么野物,整个院子血腥淋淋,又成了地隧道道的猎户了。人们也发现他越来越像一只老狐狸了。
转眼间,十年已往了,农村实验 了刷新 ,包产到户。狐爷的一亩三分地,没法种,就转包给别人种了。他一边狩猎,一边销售 皮毛,日子过得也不错。村里的有些人看到养狐狸赚钱,就纷纷养起来。邻人 张奶奶的儿子也办了个狐狸养殖场,养了一百只狐狸。有一次,狐爷对张奶奶玩笑 说,“以前我曾经说狐狸也是你的祖宗,是这么回事吧?”
张奶奶说,“这么多年的事都记得,你真是只老狐狸啊!“
村里养狐狸的越来越多,狐爷爽性不狩猎了,开了个公司,专学生 意 狐狸皮,生意也越来越大,最后建设了养狐专业相助社,日子也徐徐活泛起来。
狐爷成了真正的狐爷了.....
亦凡,山东昌邑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小说作品集《凤凰山轶事》、诗歌作品集《精灵》、随笔集《飞鸿印雪》、古典诗歌作品集《古风犹存》。
壹点号陌优势 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