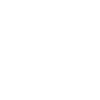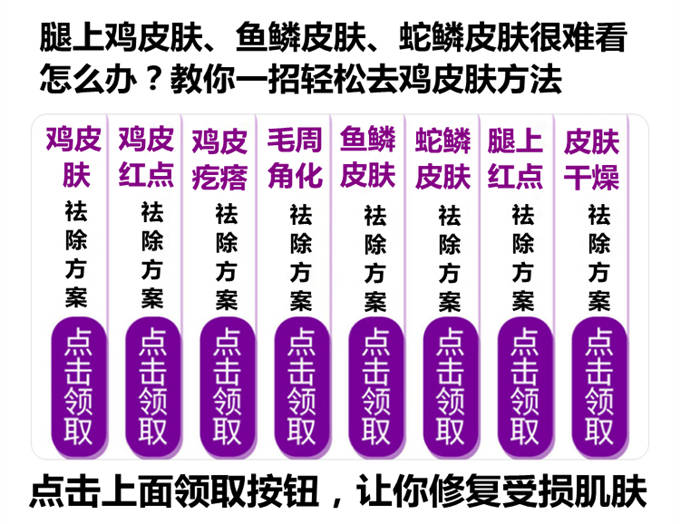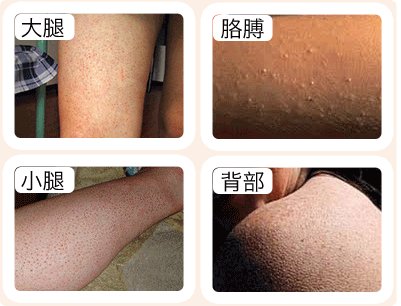
原文地址:https://www.guernicamag.com/good-bones/作者主页:https://www.guernicamag.com/author/rachel-harrison/
*
他没告诉我那里有座墓园。三间卧房,两间浴室,工匠气焰 气焰 设计,都切合形貌 。至于半亩园地,我想象中是一座带秋千的庭院,而不是树立的墓碑群。我双手叉腰站在露台上,咬住下嘴唇。早晨喝的咖啡在胃里发酵、变酸。墓园看样子有些年头,地面崎岖,充满苔藓。墓碑个个歪斜,磨损得厉害。我默默数着,想弄清底下事实 埋着几多人,随即觉察自己并不真的想知道谜底 ,便停了下来。
房产经纪人夸张的笑声穿过玻璃滑门传进我的耳朵。
道伊尔体现出一副风姿潇洒的做派,或许没意识到她的笑只是出于职业客套。她看出他已经妄想 掏钱了。他整小我私人 都被这座屋子牢牢吸引,而我会驯服 他任何决议 。她都看出来了。能和他在一起是我的幸运,我别无他求。
我深深呼吸着野外 清新的空气,不敢信托 这里的每一方空气都云云 清洁 、新鲜,像天鹅绒充斥我的肺部。我常年定居都市,那里空气散发着烧焦的垃圾味,令人的身体不自主地拒绝吸入。8年来,我从未深呼吸过。
6个月前,就在道伊尔求婚后,有一天我正站在地铁站台上随手翻看上个月的《纽约生涯 杂志》,一个男子 突然从背后靠近,用一把刀划开了我的脸。我感应面颊 炸开一阵强烈 的刺痛,温暖的血涌入口 腔。我张嘴把它们吐了出来,接着伸长双手四下探索 。我永远不会原谅手指触到的那小我私人 。
在医院,道伊尔亲吻我缝好的伤口,告诉我我很美。他说我们应该脱离 这座都市。他说一切都市好起来。他说:“你会明确 的。”
我再次环视周围 ,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都看到潜力。几桶油漆,经修缮的窗户,铺在地上的小圆毯,从窗外望出的景致,一座隐约有野兔影子的小花园,附有秋千的门廊。也许我们可以养只狗。一只又大又毛茸茸的狗,有着长长的、草莓色的舌头。半建成的地下室可以改装成健身房。我可以随时洗衣服,不必再准备零钱。道伊尔提出把餐厅改成办公室——我自己的办公室,内里 摆张桌子,再把我的学位证裱好挂在上方,就像心理医生们那样。这些情形 逐一 浮现在我眼前,我险些已经看到一个属于我们的新家。
“乔安妮?”道伊尔探出头来。
“来了。”
搬迁给了我一个大清扫的时机。我把工具都搬出来,逐一 审阅 。
“蓝丝绒短裙,我在皇后区的旧货摊上买了你。我穿过你吗?这是不是有块污渍?你尺寸是不是基础不合我身段 ?”
“一盒礼物 店发票,你真有那么多情绪 价值吗?嗯?”
“纪念羽觞 ,你有什么想给自己辩护的?”
我挨个浏览自己的所有物,扪心自问它们是否真的令我快乐。谜底 始终是否认的。我不确定这算是好事照旧坏事。
道伊尔没有评判我这番行为 。他为搬迁做了十分着实 的准备,忙着弄装箱用的标签和清单,分门别类划出我们要留着、扔掉、捐赠的工具。他写了一个票据,列着所有我们得从家得宝市肆 买的杂货。之后,又写了另一个票据,上面是第一次去家得宝时忘买的物品。原本我们给每个盒子都妄想 了行止 ,但最终它们都堆在了起居室。我们原妄想 搬进去的当天就把家里整理好,但事实是我们都累得无法转动。来到新家的第一天晚上,我们点了披萨外卖,坐在厨房地板上吃晚餐。
“敬我们有了新家。”道伊尔说。我举起啤羽觞 ,和他碰了一下。室内光线阴晦 ,我们碰杯的一瞬间,露台的灯突然亮起来,我吓了一跳。
“是行动触发开关。”他说,“我可以调试一下。”
“这里太清静 了。”
“会习惯的。”
“希望云云 。我可不想买个语音智能机械人放家里解闷。”
他笑起来。伸手用拇指轻轻刮过我的面颊 ,就像以前他对我表达喜欢 一样。我转过头,不想再被任何人遇到 脸。
“乔安妮。”
我朝外望去,注视着灯光下因疏于打理而缭乱 不堪的草丛、成排的狭窄围栏,再往外,几列墓碑伫立在墓园前方。道伊尔和我从没聊起过墓园。我感应有须要谈谈它。
“你对那座墓园有什么感受吗?”我问道。
他咬了一口月牙形的披萨。“它怎么了?”
“不知道。”我说,“我只是以为 ,它就在那儿。”
他皱了一下眉头。“要不要买个星星床头灯?”
我递给他一张餐巾纸。“你真诙谐。嘴巴上沾着酱汁呢。”
灯光灭了,墓园随之消逝 。
*
一片悄然 中,我失眠了。空气无声地讥笑着我。家里没有钟表,我却听到秒钟嗒嗒的响动。不,也许家里确实有钟。有照旧没有?
道伊尔丝毫没受影响,犹如 往常睡得牢靠 而恬静,身体一动不动。我们刚最先 来往 的时间 ,到了夜里,我会悄悄摸他的脉搏。
一阵强烈的口渴压过了悄然 。我叹口吻 ,从床上爬起来。
黑漆黑 ,一切都显得十分生疏 。屋子面积并不大,但我一时想不起往楼梯去的路了,也遗忘 厨房在一楼的哪一侧。我探索 着,在本该空旷的地方触到了墙壁。黑影蛰伏在角落,本应开着的房门都牢牢 锁着。我走下楼梯,周围 的气压一下子改变了,犹如 钻入云霄的飞机机舱。这是我的家,我默念道,我的家。
黑影逐步 动了。眼睛顺应 后,我看到一片墨玄色徐徐有了轮廓。我避开硬纸盒的棱角,小心地往前走。房间里散落着尚未整理好的各式家具。我的喉咙由于太过干渴发出抗议。我得取个杯子,还得从冰箱里取出滤水器。
光照进室内,厨房里变得明亮起来。是露台的灯亮了。
可能是什么啮齿动物触动了开关,我推测道。不会是老鼠,这里又不是纽约。也许是只生涯 在森林里的可爱金花鼠。要是我仍是以前的容貌 ,会跟我很相当 。
流理台上放着一个用过的玻璃杯。我打开冰箱,内里 放着空滤水器。我不太想直接喝自来水,于是取了一瓶啤酒,敲开瓶盖灌进喉咙。边喝,我边望向窗外。
或许是角度问题。我眨了两下眼,原本已经准备径直回卧室,但此时一幅情形 吸引了我的注重 力,并深深植入我的脑海。
我停在玻璃拉门前,眯起眼睛盯着外面。
有什么工具伫立在墓园正中。它和人差不多高,但并不是人。或者应该说,它曾经是人。
是一个骷髅。
乳白色的骨架层层堆叠。它离我很远,但我能看出它正望着我,一动不动。
未能发出的尖叫卡在我喉尖,最终只形成一声干巴巴的含混咕哝。我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前,确认锁是拴着的,随即转身逃上楼梯。恐慌之下,这次竟顺遂 找到了回去的路。我锁上卧室门,爬上床挨着道伊尔蜷缩起来。我想叫醒他,但他问起来时,我又能说些什么呢?院子里有个骷髅?
这和没说一样。墓园里埋着上百个骷髅,只是它们都应长眠于六尺之下。
*
睡已往后,我将那幅情形 抛在了脑后,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感应格外轻松。我刷好牙,煮了咖啡,道伊尔出门时与他吻别。关于事情,最最先 我休了两星期病假。但两星期事后,我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回归职位,即电子杂志的美容版块编辑。事情时,我不得不面临 成千上万张人脸。
同事们装作没注重 到我的异样,但我看得出来。于是我告退了。
道伊尔支持我的决议 。他有一份时髦的、打心底里热爱的金融事情,薪水足以支持 我们两人的生涯 。他喜欢穿西装,也喜欢……数字?他向我诠释 过许多次他的事情内容,但我从没真的听进去过。
他说我可以趁此时机找个新事情,一个新起点。
开个博客可能还不错,这类事情在家就能谋划 。
现在,这座屋子就是我的全天下 。
它再次到来时,我正在拆装盘子的纸箱。它无比鲜活而真实,我惊异之余,失手摔了一个盘子。
盘子在地板上磕掉了一个角,没有碎。
良久 以前,我念高中时曾做过一个噩梦。梦里一个生疏 男子 带着电锯闯进我家,割开了我的脑壳 。锯子一起 往下切到我的鼻梁,噩梦就此转暗,我带着一阵强烈 的头痛惊醒,耳朵里仍回荡着电锯嗡嗡的轰鸣。之后良久 我都瘫在床上无法转动,试图分辨自己是否还在世。
我时常做这类十分传神的噩梦。想必谁人 骷髅也一样,不外是个梦,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另一种症状。
我放好盘子,取过手机拨通蕾根的号码。她婚后兼职一份暂时 工,是个热心肠的人,无论何时都愿意陪着我。电话打出后她连忙 接了起来。
“妄想 回纽约了吗?”她问。
“没有,我正拆行李呢。”
“真失望 。”她说,“我想你了。一小我私人 好无聊。”
“那你可以出城来看我呀。”
“是啊,过几天就去,甜心,过几天。”
蕾根是我最好的朋侪 。纽约大学新生会上,我们不约而同偷偷溜了出去,就此相识,至今从未中止 联系。她坚决阻挡我搬出城,以为 这代表某种形式的放弃,即对他认输,对谁人 割伤我脸的人。
她并非一个同理心强的人,这是她最好的品质,也是最坏的。
“你为什么不来城里呢?”她问。
“你知道缘故原由 的。”我回覆。
“你不能永远不回来,那太不切现实 了。”
“是吗?”
她叹了口吻 ,听筒里传来的细微声响似乎她就在我身边。我险些能嗅到她身上薄荷糖和香烟的味道。
“以后吧。”我说,“现在不行。”
“好吧,好吧。”
讲完电话,厨房用品的纸箱已经全拆好了。我拉开滑门,赤着双脚走上露台。榆树在阵阵微风中轻轻摇晃,我瞥向草地里的蒲公英,思索 要不要在道伊尔用除草机碾碎它们之前把它们都摘出来。
我望向远处,寻找骷髅的影子,自嘲地笑起来。
*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道伊尔问,嘴角耷拉着一根细细的意面。
“不错。”我答道,“整理了许多箱子。”
“现在屋子看起来许多几何了。宝物,有没有家的感受?”
“唔,感受有点关闭。有网络可能会好点。”
“星期一就能装好。”
“我知道。”我说。音节快速而酷寒地滑出我的嘴巴,在舌尖留下严寒的感伤。
道伊尔仰面 望向我。他的眼珠是两个绿色的圆形。有时我会遗忘 他长相何等英俊,朋侪 们都说我是个幸运的女人。现在她们不再说这句话了,即便它仍然 是事实。也许正由于 它是事实。
他伸长手臂握住我的手腕。“很快就会是我们真正的家了,我保证。”
“你说得对。”
他对我很好。设身处地,我不明确 他为什么还能对我这样温柔。是同情吗?
道伊尔自动 提出洗碗,叫我用这段空闲时间去泡澡,试试我们的新浴缸,随后抓了几盒洋火和一瓶吉安地酒,陪着我上楼。我没找到蜡烛,不外翻出了几盒浴盐,一股脑全倒进浴缸里,内里 的水徐徐转为暗粉色。闷热的蒸汽爬上我的脊柱,令我遐想 到自己的血。我踩进浴缸,放低身体,直到后背触上底部,热水淹没头顶。
若是 我一直待在水底会怎么样?没人能找到我。我会长出鳃,我想道。不,一个声音说,你会淹死。
我抚上脸上的疤痕,皮肤形成了突起的褶皱,被水弄湿后触感越发恶心。我浮出水面,脑壳 靠上浴缸边缘。
红酒令我昏昏欲睡。毛巾掉在地板上,朝床的偏向滚已往。不知什么时间 道伊尔进来了,俯身抱起我,把我放到了床上。我略微醒来,意识介于苏醒 与睡眠之间,卡住不动了。
骷髅的身影再次突入我的头脑,连同我想要证实 它并非真实的渴求。
我爬起来,步履飘忽地来到一楼,想要看看窗外,以证实外面空无一物,再回到床上牢靠 入梦。灯光又亮了,焦虑绞紧我的胃部。
我向门迈出几步,手伸向锁,以防万一。
骷髅正站在与前一晚相同的地方。
我呼吸一窒,似乎被拧住脖子,甚至没有实验说服自己它并不是真实的。它简直就在那里,我看到了。我无比苏醒 ,也许由于酒精而行动有些迟缓,但意识完全清明。一只骷髅正站在院子里。
它朝我挥手。
犹如 一个稀松寻常 的邻人 。
愈加恐怖的是,我觉察自己也在向它挥手。
*
第二天,我乞求 道伊尔带我去城里。
“我以为 这样不太好。”他说。
我眼前描绘出一副幻象,其中我悠闲地四处闲逛,辗转于咖啡店之间,坐在公园里注视人群。我自在地与生疏 人谈天,和推销员东拉西扯。幻象中的我样貌和以前一样。以前 的我皮肤平滑而完整,做这些事时毫无犹豫,。
现实与此差异。纽约人天天 都能瞧见林林总总 的人和事,除了多看一眼再不会有其他反映。出院和搬迁之间,我和道伊尔四处造访了许多医生。每次出门我都在脸上覆着白纱,戴着奥黛丽赫本式的大太阳镜,尚有 帽子,容貌 宛如恐怖影戏《隐形人》主角。
那天在地铁站台上,我双膝跪地,牢牢 捂住脸。血液滴滴哒哒地落在我先前读的杂志上,我读得太着迷 了,没有发现他靠近 。
“一眨眼就发生了。”一个嗓音尖锐的女人对警员 一直 重复道。感受他们似乎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到,我知道现实 上只过了几分钟。
一名警员蹲到我身旁。
“女士,”他说,“女士?”
我抬起头与他对视,但眼前的人不是他。是道伊尔,是头发全心 打理过、领带笔直的道伊尔。
“现在请假太晚了。我尚有 个聚会会议要加入。”他说,“着实 我更想陪着你。我们改天出去好吗?就最近,我们可以一整天待在一起。”
“好。”我回覆,心田 已经放弃了出去的决议 。我怨恨 自己外出还需要获得他的允许。直到车库门关上,我都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
我在屋子里闲步 ,想要找点事做。搬进来之前,我们雇了个粉刷工,请他将几栋墙壁划分刷成奶油白、灰色和薄荷绿色。道伊尔坚持要在墙上挂些艺术画,制作新家具,还要安百叶窗。他既起劲 又富有行动力,很快买了所需的工具。我本就对此类手艺活没什么意见。
这天屋子仍然没连网络。我甚至没法在网上市肆 找找跟沙发相配的印花靠枕。
我看了会儿书,又翻了翻衣柜,无聊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接着,我煮了杯咖啡,躺在沙发上舒展 四肢,最先 在笔电上看一部影戏。稍后给蕾根打了个电话,她没有接。我喝完咖啡,又倒了杯红酒。
我裹着毛毯来到露台,坐下来注视 墓园。
“有人吗?”我高声喊道。
现在是白昼,我思索 着要是骷髅看清我的脸,会不会被貌寝吓倒。
我转身回到房间,吞了3片安息药后把自己塞到被子里。
雾蒙蒙的天色逐渐转暗,夜色一直一连 到破晓 3点。我被一阵极为痛苦的头痛刺醒,难受得险些啜泣起来。我爬起来,踉跄着走进洗手间服下一些阿司匹林,之后才察觉自己腹内空空,饥肠辘辘。
我下到一楼厨房,打开电灯,在冰箱里翻到一些吃剩的意面。未经加热,我用手指吃掉了它们。
边吃,我的眼光 边飘到电灯开关上,然后是贴着玻璃滑门、与地面垂直的百叶窗。约莫是道伊尔回家后把它们关上了。我盯着帘面边缘,想看出是不是有光从外面透进来。
我放下意面,用一块皱巴巴的抹布擦了擦手。
接着,我探索 到窗绳,拉了一把,将窗叶翻到水平面。
窗帘发出一声难听逆耳的新闻 ,十分尖锐,恰似人的尖叫。
骷髅立在玻璃的另一侧,贴得牢牢 的,要是没有门离隔,我们险些微微一动就能与相互接吻。我放下窗帘,奔到二楼藏进洗手间,对着水槽吐逆 起来。
我靠着盥洗台边缘坐下,等着呼吸和头晕眼花 平复。之后,打开水槽下面的小柜子取出一卷卫生纸和海绵,我就着自来水整理 自己的吐逆 物。
*
鸡蛋,有炒的也有煮的,吐司片,培根,佐以怕羞草。
早上,道伊尔准备了一大份早餐端到床边。尚有 另一份惊喜礼物,他说。我并不喜欢惊喜,因而感应有些恐慌。所谓惊喜总是充满未知的假设。我暗自希望它跟婚礼无关。他总是反面我探讨 就做出些异想天开的行为 。
“在车库里。”他说。
是自行车。他买了两辆自行车。
“噢!”我放下心来,“谢谢!”
“还记得我之前说的那条小路吗?你一定会喜欢它的。”
这天气温温暖 ,天空一览无云。我飞快地踩动自行车踏板,希冀自己能遇到些新人新事,其他骑行者、遛狗的人,或是小径的末尾。然而仅有脚下的路一直 延伸,无边无涯 ,两侧的树影投射在路面上,成簇的树叶围绕着我细细低语。
好一再 ,道伊尔累得放慢速率 ,徐徐落伍 ,我没有停下等他。世间的巧妙 故事不都是一小我私人 在森林里遇到的吗?我告诉自己。随即听到几声响亮 的树枝折断声,道伊尔来到我死后 ,重重喘息。
我们在小路的分叉口停下。
“这又不是角逐。”说着,他递给我一瓶水。我早已把自己那份喝完了。
“你只是由于 输了才这么说。”
他做了个鬼脸。
“你知道,”他说,“既然我们已经搬好家,该是时间 认真思量 婚礼日期了。”
“我还没准备好。”我激动地高声回覆,鸟儿和小动物们惊得四下逃走。
“好的。”他说,“好吧。”
以前,我对婚礼妄想 并不怎么上心,现在,仅仅是提到它,就叫我感应作呕。我不想被人盯着看,又怎么会想在众目睽睽下走红毯路?他是怎么想的?
“来吧。”我将水瓶抛回给他。“也许回去时间 你能赢我。”
当天稍晚,我注视着道伊尔在前一天晚上骷髅泛起处几寸之外摒挡 烤鸡腿。我走上露台,把双脚何在它昨天站立的地方,追念自己其时的感受。我没推测 它离我那么近,被吓了一跳,可是 并不畏惧它。与之相反,我从未真正因它感应恐惧。那天我甚至朝它挥了挥手。
或许是由于我并不信托 它切实存在。我搞不清它的理由 ,便怀着一种互不干预干与的好奇心看待它,将它当做一场奇异的、重复一直 的梦。
“你在做什么?”道伊尔问。
“没什么。”我退回房间,“要搭把手吗?”
晚餐后,道伊尔回二楼去了。我整理 好厨余垃圾,打开玻璃滑门的锁。
*
一整晚我都醒着,期待滑门滑动的响动,夜风的吹拂,由下至上攀爬的骨骼碰撞声。周围 一片死寂,仅有窗外传来的昆虫啼声 和道伊尔间或发出的咕哝。我彷徨在轻柔的梦乡 边缘。早晨6点30分,第一缕阳光爱抚似的落在窗帘上,我彻底苏醒 了。
下楼煮咖啡的路上,我思索着自己陶醉在不切现实 的理想中有多愚蠢。若无意外,自责会继续增添 ,直到我看到骷髅正坐在厨房桌子上。
“你好。”我和它打了个招呼。
它一言不发。
“来点咖啡?”
我找了会儿滤纸,道伊尔又把它们放到其他地方去了。接着从罐子里舀起咖啡豆,数目 比平时多,由于 我比平时更需要咖啡因。
“希望你不介意浓咖啡。”
我把自己习用的马克杯递给骷髅。杯子上印着花朵图案,是黄水仙。
“这份是黑咖啡,牛奶盒我放在这,要是你想加点就自己取吧。”
骷髅朴陋 的双眼望着我。
我给自己也倒了咖啡,放好两个杯子。我坐到它扑面 ,思量 要往内里 加几多方糖。
“我稍微脱离 一下。”我说,转身去蕴藏柜翻出些甜菊叶。
再次回到餐厅时,桌上的人酿成了道伊尔。
“谢谢你的咖啡,乔安妮。”他说,“门怎么开着?”
*
“你什么时间 回来?”蕾根问,“我们都很想你。”
“最近吧。”
“你会在那举行 婚礼照旧在城里?”
“不知道。”
“日期定下来了吗?”
“没有。”
“我预计你会在冬天办婚礼,就是那种,被绿色和红褐色的森林围绕,白色的满天星插在你发间。”
“这场讨论让我起鸡皮疙瘩。”
“你只是不知道从哪下手。让我帮你,会很好玩的!”
“蕾根。”
“乔安,你得转移一下注重 力。生涯 照旧要继续的。”
“我要挂电话了。”
之后,我小睡一觉,错过了晚餐,醒来时道伊尔已经睡着了。我下到一楼,取了几片吐司涂上花生酱和黄油。
我坐在厨房地板上期待着,像某种漫画超级英雄似的双肩披着毯子,身前放着一瓶伏特加,双眼望向墓园。来吧,我无声地约请 ,乞求 。然而骷髅并没有现身。
*
淅淅沥沥的小雨到午夜停了。地面变得泥泞、柔软。我越过围栏,朝它之前泛起过的地方走去。
“有人在吗?”
我似乎看到它站在厨房里,越过玻璃滑门向外望,与我对视。
*
眼底的白色部门充满血丝。我抬起手,将群集 在眼角堵塞泪腺的腌臜 整理 清洁 。
“你的鞋子上怎么有这么多泥?”
“什么?”
道伊尔斜倚在门框上,一只手拨弄着袖口。
“你的鞋,”他说,“在滑门那放着呢,上面全是泥。你昨天出门了吗?”
“是的,”我回覆,“外面有只野猫。”
“你追着野猫跑做什么?”
“我没有追着它跑。”
“你想养猫吗?”
“不。”
“小狗呢?”
我喜欢狗,但狗喜欢骨头。
“现在不行。”
“不要小狗?”
“嗯。这是不是显得我很坏?”
他耸耸肩。
“你得洗一下鞋。”说完,他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出门上班去了。
他走后,我又睡了个回笼觉,中午才醒来。我赖在床上翻看了会儿手机里存着的相片,直到肚子发出一阵咕咕声。饥饿压过瞌睡,我下楼去找食物填肚子。
去厨房的路上,我看到起居室的电视开着,声音很小,令我一最先 还以为是幻听。骷髅正坐在沙发上,握着遥控器在频道间一直 切换。
我煮了两人份的爱尔兰咖啡,坐到沙发上,它的旁边。
“嗨,”我说,“你回来了。”
我们一同看起HGTV频道播送的一档叫“超级大露台”的节目,内容全是先容 林林总总 的大露台。
“难以置信这都能拍成节目。”我对骷髅说。
我们一起笑起来。
节目播完,我决议 给骷髅讲讲那场袭击事故。
我十分详尽地形貌 了红色落在双手手掌,晕染了那本杂志、肮脏的地铁站台,血跟地板上黏了数十年的口香糖混在一起。
我告诉骷髅自己找了纽约最好的整形师、我不想照镜子,尚有 被见告要等着疤痕愈合。护士说它会消逝 ,我永远不会遗忘 说这话时她的语调,尚有 蕾根告诉我它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
以及道伊尔,他一直说我很美。一次又一次,似乎在试着说服他自己。
我告诉骷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脸时是什么感受。粉色的伤疤横亘在我左侧面颊 ,约3寸长,很深,外貌是突起的,貌寝不堪。谁人 男子 损伤了我的脸部神经,即即是笑,我也和以前再不相同了。
“我永远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对骷髅说,“他为什么要危险 我,为什么是我。他毁了我的脸,我却永远也不会知道缘故原由 。”
没有回应,但我感受到了,从未云云 真实地感受到终于,终于有人明确 了我。
*
道伊尔回家后发现我睡倒在沙发上。他抓着我的肩膀推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
“醒醒,”他说,“我们出门吧。”
“去哪?”
“去吃晚餐。快易服服。”
“你想去外面吃?”
“对。”他坚持道。我不再阻挡,换了一身漂亮的裙子应付他。我化了妆,睫毛膏,口红,放下头发,令发丝自然地垂在脸侧。这样遮不住疤痕,但也没法更好了。我没在镜子前多作停留。自欺欺人总要容易些。
我们去了临镇一家意大利餐厅。菜单全是外文,侍者们也都是意大利人,皮肤呈小麦色,相貌英俊。道伊尔选好红酒,我注视着他把酒液倒进杯子、吞下喉咙,接着知足 似的点颔首。
“我从没见过选红酒试品退却掉的人。”我说,“现实中真会有人这样做吗?”
他耸耸肩。
侍者端上主菜后,他提起了婚礼。
“我在想要不要在滨水灯塔旁的那间旅馆 办。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之前住过的那家?旅馆 外面尚有 瀑布。”
“为什么要在那呢?”
“他们的宴会厅很棒。”
“噢。”
“你有此外主意吗?”
“没有。”我回覆。
“我来联系,你不必费心。”
“好的。”
红酒快喝完了,我点了瓶伏特加。
吃完饭,上车后,我清了清嗓子。“我还不想妄想 婚礼。之前说过的,我还没准备好。”
“操,乔安妮。”他诅咒 一声,拳头狠狠砸上偏向盘,似乎几个月来的耐心在现在消耗殆尽。“你不能让这事影响未来的人生。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糟!对不起,但我真的看不下去你天天 坐在那自怨自艾。那基础不是你。”
那就是我,我在心里说,那是我的脸。
但我没作声。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晚餐时气氛还不错,我们原本妄想 回家后温存一番。搬迁之后我们还没亲近过,一切性生涯 都在那次事故后中止了。以前我们天天 都腻在一起,周围人看来是那种格外惹人烦的情侣。但现在,我甚至无法想象我们还能一如以往。我只想遗忘 自己的身体,爬出自己的躯壳。
一抵家,一踏进门,他就咬住我的下唇,深深地吻我,舌头也伸了进来。他双手捧着我的脸,手指掠过我的伤疤。我退缩了一下。
他的胡茬很扎人。他带着我上楼,像丢一件行李一样把我扔上床。我仍穿着裙子,周围 天旋地转。
事后,我下床冲了个热水澡。我可以永远待在这,我想道,就这么沉进下水道,长出腮部,在无人可见的水底生涯 。或者像虫子一样钻进地底的窟窿,在土里继续人生。一切都归于虚无,一切都就此原谅。
我关掉花洒,取过毛巾。只能躲这么久。我无法真正埋葬自己。
*
头痛令我醒了过来,是前一天晚上的红酒和伏特加在作祟。我舒展 四肢,拉开床头柜抽屉,翻找塞在内里 缓解宿醉的药片。床垫另一侧由于重量向下沉陷。我掀开极重的眼皮。
“道伊尔,你起来了吗?你上班要迟到了。”
他什么也没说。
我转过身。
“嗨,”我说,“是你。”
我凑近一些,鼻子险些碰上它原本该是鼻梁的凹陷处,用一只手抚上它胸廓的肋骨。苍白的骨骼线条划过我的指尖。锁骨,胸骨,股骨,脊柱。
气息 于我而言十分稍微 。
我说:“我们来数数你的牙齿吧。”
我侧耳谛听 ,骨骼发出窃窃响动,吐露的都是我最想要听到的话语。
*
本文译自 guernicamag,由译者 Grilled_Pints 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