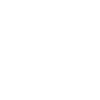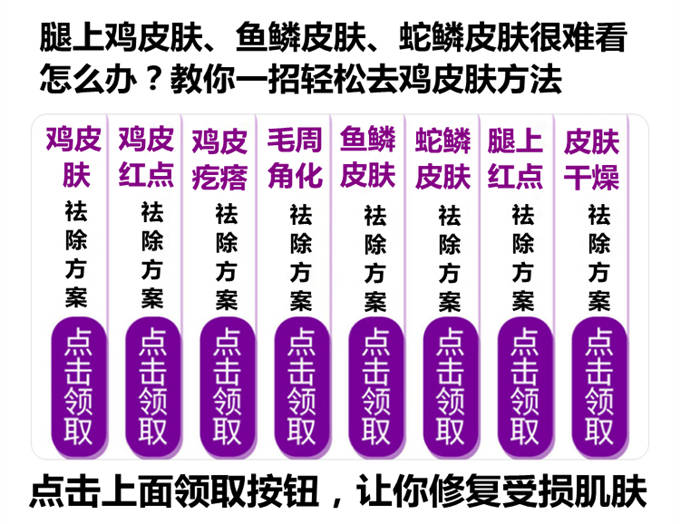1
我最爱吃的就是包子,发酸的也好。一边吃着,一边摸了摸自己瘪瘪的荷包,闲着无聊,把里头的仅有的几个铜板倒了出来,在手上依依不舍地把玩来,把玩去。
现在 这物价水费增添 飞快,连包子哥的那家包子铺里的那种丢给巷子里的招财都不愿理的馒头都每个涨了两个铜板,那对于我这种每个月月薪只有三十个铜板的小捕快真是一种精神折磨!天天 数来数去,翻来覆去,巷子里的招财都生了一只进宝了,我的月薪照旧不见涨。
这仅有的几个铜板,照旧我在县衙的好哥们李睛友谊 赞助给我的。
这都该怪县太爷太抠门……不,是县太爷要养的夫人可堪比当今圣上的三千后宫,里一堆,外一大堆,自己的九品芝麻俸禄不够,就只能苛扣我们这些小跑腿的。
我一边哀怨地啃着肉包,一边看着自己租住的这栋老宅,内里 的工具已经被房东的妻子 ——肥墩,唔,这是我给她取的外号,却从来没有谁人 狗胆当着她的面这么叫她。
现在 的我落得云云 下场,缘故原由 是我已经拖欠了肥墩三个月的房租,而且在她每次来收房租时都是秉持着知错就认、下月交租、打死不改的精神,她在昨天又收不到房租,一怒之下搬走了老宅里所有的工具,包罗床底下已经生了一窝的蟑螂和我丢在内里 不知几个月没洗的臭袜子。
我为了自己的福利,翻身农民把赞美,举起起义的牌子,反抗道:“包租婆,你把工具都搬走了,你让我怎么睡觉啊?”
肥墩把两只粗得跟盘子的启齿 似的胳膊叉上了她的水桶腰,恶狠狠地对我说:“夏糖,若不是你是个捕快,我就直接把你这小我私人 扔出我的屋子了!还盛意 思提睡觉,睡我的床不要钱啊!”
我瞬间如被猛火 烤焦的番茄一样平常 焉了下来,只好默默地缩回龟头。
有个宅子,虽然内里 空无一物,但总比我睡大树底下造福蚊子强。这么一想,我又释然了。
肥墩这人在家里什么都敢干,凶悍得能把房东(也就是她相公)捏成算盘,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挺怕官府,怕县太爷,怕摊上事儿。一出门,就什么都怂了。
她人不坏,就是死要钱,在外头开了家寺库,还就叫死要钱寺库。
我曾司理 想过要跟把县太爷勾通过来,在肥墩的屋里走上一圈,她说不定就会把所有的床啊桌子椅子的一切我屋子里的工具都还给我,还顺便给那些在床底下被她踩死的蟑螂们烧柱高香。
可是 也就是想想。
好不容易啃完了一个包子,正要把钱收回去,外头就传来了李睛呼呼呵呵和闯进门的声音,把刚刚脱了衣服妄想 要洗个香香浴的肥墩吓得尖叫了一声。
我站起身,突然一个头晕眼花 让我不小心掉了两个铜板。我心急如焚,正要蹲下去捡,就要遇到 铜板的当头,李睛这个杀千刀的家伙,直接把我拉起来就往外跑。
我被他拉着满大街的跑,一边留着迎风泪一边尖叫:“李睛,你疯了,我屋子里尚有 两个铜板没有收起来。一会儿让肥墩望见 了,就得私藏起来了!”
李睛不以为然,转头对我说:“不就两个铜板么,我再给你一百个都行!不外这事转头再说,眼下县衙有主要 的事情需要我们行止 置赏罚 ,处置赏罚 完了我再拿钱给你。”
我很想拒绝,以体现我的高尚人格。可是 囊中已经羞涩到快为负值,在生命安危和高尚人格眼前 ,高尚人格又是什么工具?几毛钱一斤?
于是我噤若寒蝉 地接受了他的盛意 。
他拉着我到了衙门口,那里已经群集 了不少人在门口围观,纷纷窃窃私议窃窃私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一个穿着粗布麻衣,高卷衣袖裤脚,全身 脏兮兮,脖子上还挂着一顶斗笠的消瘦 男子正手持鼓槌,拼命地敲打着,敲出了一声又一声震天的响。
若是论以往,县衙里基本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平常 都是谁家的狗偷了谁家的鸡,谁家的媳妇跟谁家的相公跑了之类之类的杂事,只要我们这些小的跑跑腿就好。县太爷基础不用出来,天天 跟他的三千姨太打打马吊,从来不烦恼三缺一,日子过得滋润优美 。
可是这次又是击鼓鸣冤,又是这么多人围观,是我上任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大事务 ,整得我热血沸腾的。
李睛拨开那些堵在县衙门口的人,然后拉着我跑了进去。
里头所有的捕快都已经到齐了,只缺了我和李睛。李睛在县太爷坐上位置之前,连忙从旁边拿了两根掉漆发霉的红棍子,递了一根给我。
在我眼里,县太爷生得跟肥墩差不多,只不外一个男,一个女的而已。
他戴着一顶积了陈年迈 灰的乌纱帽,抖着身上的肥膘坐上了位置,大叫一声:“来人,把击鼓的人给本官带上来!”说罢,用力一拍惊堂木,差点把可怜的年久失修的桌子拍出一个洞来,“升堂!”
我拿着那根红棍子,一边压低声音喊着“威武”,一边一直 地用那根红棍子戳地板。
几个捕快把谁人 击鼓的人瘦小男子带了上来,押着他跪下。
县太爷装模作样地捋了捋自己的髯毛,眯缝着一双眯眯眼看着台下跪着的人,“你,可有写状子?”
谁人 男子连忙颔首,从怀中掏出了状子交给身边的捕快,捕快则是呈给了县太爷。
县太爷把那份状子倒拿着看了半天,一边看一边还意味深长地“嗯”几声,然后交给身边的师爷,细细询问:“师爷,你怎么看?”
师爷看了一遍,轻咳了两声,然后低声在县太爷耳边说了些什么。
我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瞥已往,只见县太爷听了师爷的话后,神色 大变,差点没滑下椅子。师爷用尽吃奶的实力 扶起了他,用眼神示意县太爷:“不能失了你县太爷,堂堂九品官的风度。”
县太爷与师爷眼去眉来 一番,在吸收 到师爷的爱意后,连忙肃正面容,为了示威,又一拍惊堂木,道:“既然发生了这样的惨案,你且再把详细 情形 与本官说说,本官好替你查到凶手!”
谁人 男子似乎憋了良久 了,一听到县太爷让他启齿 说明详情,就急切地说:“县太爷,小民是江边以打渔为生的张四。被害的正是小民的年芳十三的女儿,张娇娇。小民今天打渔回抵家,就,就见到我女儿全身都是血,就,就那么躺在地上……”他说着说着,便心痛地哭泣起来,“小,小民妻子早亡,就只有,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与小民相依为命,现在 ,现在 她却……”
众人大感同情,外头围观升堂的观众也都举起右手让县太爷抓到凶手,剥皮鞭尸,为民除害。
县太爷已经不知几多个年头没有处置赏罚 过这样的案子,又听到县衙外观众的呼声,禁不住 备受压力,只得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庄重 !张四,你且继续说。”
张四用那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手擦掉眼泪,“小民近身一看,发现小女的脖子上有两个血洞,还在淌着鲜血。小民,小民嫌疑 是,是……”他后面的话却哆哆嗦嗦地不敢说出来。
“你嫌疑 是什么?你倒是说呀,真是急死本官了!”县太爷敦促道,“不管是什么,你都斗胆地说,本官不会降罪于你,由于 这很有可能是破案的主要 线索!”
看县太爷云云 专业的容貌 ,张四也就不再吞吞吐吐,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回禀县太爷,小民听闻邻县,以致 邻县的邻县,都有发生过此类事务 ,被害者都是跟小女一样平常 年岁 的女子,脖子上也都有两个血洞。小民看来,是,是吸血蝙蝠在作怪,他把小女的血都吸尽了,好采阴补阳,练成邪功……还请县太爷明察!”
众人在听到吸血蝙蝠时,通通哗然了。
这吸血蝙蝠我也有所耳闻,不是那些长了同党 的耗子,是江湖上法力高强、至阴的邪物,名叫冷蝠,几年前刚归顺攻克整个江湖势力的邪教,九氤宫,为九氤宫宫主卖命。
不外么,我倒以为 这不太像谁人 吸血蝙蝠做的。缘故原由 有二。一是九氤宫离我们丰临县有一段着实 是特殊 特殊 长的旅程 ,吸血蝙蝠又常年呆在九氤宫为九氤宫宫主炼制丹药,没原理千里迢迢跑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只为了吸这几个妙龄少女的血吧?
二,吸血蝙蝠生性冷血却十分有洁癖,吸完血后一样平常 不会把猎物弄得全身 血,而且他会把血吸得很清洁 ,不似有那位张四说的什么血洞还在淌着鲜血的话。
我小我私人 以为 ,那只吸血蝙蝠一定是个龟毛洁癖万年撸啊撸的老处。
2
此时一听到吸血蝙蝠的台甫,原来油头满面两眼随时随地都散发着X光的师爷的神色 连忙 就酿成了便秘状。不外县太爷和观众正在眼睁睁地看着他,他也欠好推拒,贼眼溜了一圈,便问那张四道:“张四,你家女儿的遗体 可叫仵作去验了?”
张四连忙颔首,“验了,验了。仵作也说那两个血洞是人在入魔后衍生出来的血牙,凶手应当是吸血蝙蝠,不会有错的。”
我皱眉,却是不太认同仵作的说法。什么入了魔衍生出的血牙,这完全是迷信的说法,连吸血蝙蝠的那双血牙也是能工巧匠为他打造的,那里 有衍生血牙一说。
师爷这下可也没精打彩了,低声喃喃自语道:“可是吸血蝙蝠远在九氤宫,而且单凭我们衙门里的捕快,怎么可能捕到吸血蝙蝠那样江湖上鼎鼎著名 的大魔头?更别说,吸血蝙蝠的靠山照旧九氤宫,听说九氤宫的那一位跟皇族尚有 些牵连,在江湖上都无法无天了,岂是我们一个小小的衙门能去管的?”
我拿着红棒,低着头迈着低调的小碎步走已往,在一脸被雷劈了的师爷耳边说:“师爷,小的以为 ,这么重大的事务 应该上报给六扇门,而不是我们县衙独自肩负。”
师爷眼睛一亮,转头,给我抛了一个赞赏的眯眯眼,然后把我的想法说与了县太爷听。
县太爷的生命也一下子亮堂起来了,连忙一拍惊堂木,道:“此事事关重大,经本官和师爷讨论,决议 把这件事情上报给六扇门。咳咳,退堂!”
底下的张四的眼神看起来也有了一丝希翼。六扇门啊,传说中有四位神捕镇守的六扇门,突破大巨细小的案件无数,不知制服了几多恶人,其中也不乏悬案。只要这件事情上报给六扇门,四大神捕亲手破了这案子,还不愁他的女儿沉冤得雪吗?说不定还能获得朝廷的一大笔慰问费。
县太爷喊了句退堂后,就很灾黎 大逃亡似的,膘肥体壮的身体难堪 今天无邪 ,还卷走了师爷,飞也似的跑到后堂去了。
我看着那两人仓皇脱离 的背影,总以为 在县太爷和师爷之间弥漫着一股十分浓郁的味道。唔,这个我在花灯区内里 的鸡鸭鱼肉馆里经常闻到,我把它叫做奸情的味道。
岂非 县太爷和师爷两人背着三千姨太在小树林里暗搓搓地……唔,嘿嘿嘿。
正当我浮想联翩时,突然有人在我死后 ,轻轻地敲了我一个栗子头。虽然不痛,但我照旧龇牙咧嘴地装得一番跟脑骨断裂了一样平常 ,转身,对死后 的人说:“痛痛痛痛痛!”
李睛瞥了我一眼,“夏糖,你又跟我装蒜。”虽然说是这么说着,手却很小心地揉着我的头,神情专注,时不时地还低头问我:“还疼不疼?”
我以为 不太盛意 思,便拨开他的手,道:“不疼了不疼了,既然退堂了,我就要回去了,还不知道我那两枚铜钱有没有被肥墩捡走……”
李睛一脸无奈地看着我,然后从袖口拿出一个很清洁 的,装得满满的一个香花鸳鸯荷包递给我。
我接过谁人 贵族小姐才有的软荷包,爱不释手,翻来覆去拿在手上把玩,赞叹 :“李睛,你什么时间 用上女孩子的荷包啦,这么风骚倜傥?”一边把玩着,却突然想到了某个可能,把玩香花鸳鸯荷包的手顿了顿,然后战战兢兢 地试探道:“李睛,你不会,你不会心田 里住着一个玉人 吧?”
他一愣,不知道有没有曲解我的意思,脸竟然有些微微的发红,“你,你怎么知道?”
我恐慌 ,没想到李睛尚有 这样一个大神秘 藏在心里没有告诉我,若不是今天看到师爷和县太爷之间的奸情,我都不敢信托 这世上竟然真的有市井里撒播 的那些话本上说的男子 和男子 的惊天绝恋!可,可我就算想到了,却也没想到有此好的人那么多,我的好哥们,平时挺爷们的李睛竟然也是其中的弯男?!
那些市井里的话本说得都十分委婉,就是两个男的之中饰演女性角色的谁人 男子 ,通常心田 里头都住着一个漂亮 的女子,驱使着他与另一个男子相爱。
以前总以为 这些不入流,又不能被世俗所接受,都只是那些书商书贩杜撰的,或者是有一些有此癖好的人写下的猥琐话本,却万万没想到……
我最先 好奇地审察李睛的外貌。果真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不看还好,一看还真是要吓一跳。以前我总以为 李睛很爷们,或许是由于 他的某些行为很爷们,可是现在 细细看来,这李睛倒也算是个俊俏人物,白面书生但绝不奶油,很像那些进京赶考却总是住到鬼庙然后被女鬼骗才骗色的书生。
这么一来,李睛确实也切合话本中所形貌 的那样,白皙可人。虽然没有细皮嫩肉,也没有唇红齿白,可是 也算是有几分姿色的,至少跟我们衙门里的那些歪瓜裂枣比起来,那可称得上是衙草一棵。唉,一想到好兄弟也早晚要被此外男子 大炮攻城,失、身陷落 ,我心里就忍不住大叹惜 惜 呀!
李睛看我入迷了一盏茶的时间,挑眉道:“夏糖,你在想什么,想了这么久?”
我的脑中已然浮起某些老小 不宜的绯色画面,索性李睛看不到我在想什么,否则定要将我五花大绑然后敲坏我的脑壳 的。
听到他叫我的名字,我瘪嘴,“别叫我夏糖,我一个女子,被怙恃取名为‘下堂’,也真是有够衰的了,你还要来踩我痛处。”
李睛的眼里泛着我所不知晓的光泽,语气似乎带着点隐约 的兴奋和期待,道:“原来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我不唤你全名总以为 有损你的清誉,不外既然你不喜欢我叫你全名,那我便唤你‘糖糖’,怎样 ?”
我不怎么介意他这样叫我,叫“糖糖”反而把我衬得年轻了许多,也就随口道:“你想怎么启齿 叫我,便怎么启齿 叫吧。”
他似乎有些激动,语气含了隐约 约约,若隐若现的欢喜,唤了我一声:“糖糖,我送你回去罢。”
听到他这么叫我,莫名的,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转头,看了看他那在我眼中显得有些诡异的笑容,本想拒绝的,可是 回过头想想,我刚收了人家那么一大袋铜板还不知银子,这么“绝情”有点不太好啊。
于是,我大大方方地跟他勾肩搭背,豪爽地说:“走吧!”
他一最先 也曾呵叱过我男女授受不亲、女孩家的清誉之类之类的屁话,可是 厥后我屡教不改,他也就屡教接受了。
回去的路上,他突然问我道:“适才谁人 上报六扇门的主意,可是你想到的?”
我咧嘴一笑,自得地说:“是啊,否则怎么办,这类案件也不是我们这种小县衙能够破得了的。”
他噗地一声笑出来,道:“若是 凶手真的是吸血蝙蝠,那你也可真是难为六扇门了。”
“这话怎样 讲?听闻六扇门的四台甫捕十分神力,他们每小我私人 单独拎出来,武功在武林中算得上顶尖能手 了。吸血蝙蝠就算再厉害,也终究是邪不胜正的!”我夸夸其谈,提起此事,心中
又有一丝丝难以言说的落寞。
“你是真不知照旧假不知?吸血蝙蝠是九氤宫的人,放眼整个江湖、整个朝廷,也没有人敢去冒犯九氤宫。九氤宫的那位的手段和武功不是你能想象的,”他摇摇头,“听闻他已经好几百岁了,两百二十岁之时建设了九氤宫……”
我瞪大了眼睛,将信将疑地问:“真的有人可以活到那么久吗?”
李睛但笑不答,停下了一直向前迈的脚步,把我勾在他肩上的手扒开,指了指肥墩家,道:“糖糖,你抵家了,改天我们再聊。”
我一听到这种江湖大八卦就停不下来,听到他要走,垂下头,不禁有几分气馁道:“那你明天来叫我去衙门时可要继续说给我听啊!”
他点颔首,笑着说:“我保证说给你听,现在快些进去吧。我走了。”
我“嗯”了一声,然后朝他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肥墩家。
李睛一直在我死后 站着,直到我进了自己那间空荡荡的老宅,他才放心地转身脱离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了。
着实 若不是情非得已,我真的不想再面临 这一贫如洗 的惨状。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再看看空荡荡的地,果真那两枚铜钱被肥墩顺走了。
我拿出李睛给我的谁人 香花鸳鸯荷包,拉开来一看,内里 的工具差点没闪瞎了我的老眼。
我说这荷包怎么那么沉,原来内里 都是碎块的,利便 我取用的银子,尚有 女人家戴的一些珠宝首饰。此时现在,我严重嫌疑 ,要是这个荷包再大一些,李睛也许还会再给我塞上两盒胭脂;要是这个荷包再再大一些,他也许会给我塞两件女人家穿的衣服。
哎呀,兄弟啊,难为你破费了……
我一边笑得牙不见眼,一边数着内里 的银子。内里 的银子着实 许多,笼统数来或许有十两左右,都够我花销个一两年了。
不外看着那堆漂亮的看起来很昂贵高等次的首饰,我有些发愁它们的行止 。一来,我是捕快,随时随地都要到衙门去的,县太爷划定,女捕快不行以戴首饰去衙门,否则一切 没收。二来,我也没有漂亮的衣服或者说像样一点的衣服可以和这些悦目的首饰搭配,更没有闲钱去买衣服。就算李睛给了我这么多银子,那我交肥墩的房租,我还得一日三餐,我还得……支付许多许多我现在说不上来的用度。
眼下我的收入与支出显着 呈负增添 的趋势,不攒些银子过日子那一定 是不行的。
依依不舍地从荷包里数了八钱银子,然后把荷包收好,捏着银子去找肥墩交房租。之前我已经欠了三个月的房租,那顺便也把这个月的房租给付了罢,一个月二钱,肥墩总是 把房租往贵了收。
我走到了肥墩的屋外,正要敲门进去交房租,突然——
小说后续章节,直接戳下边:相识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