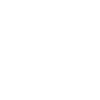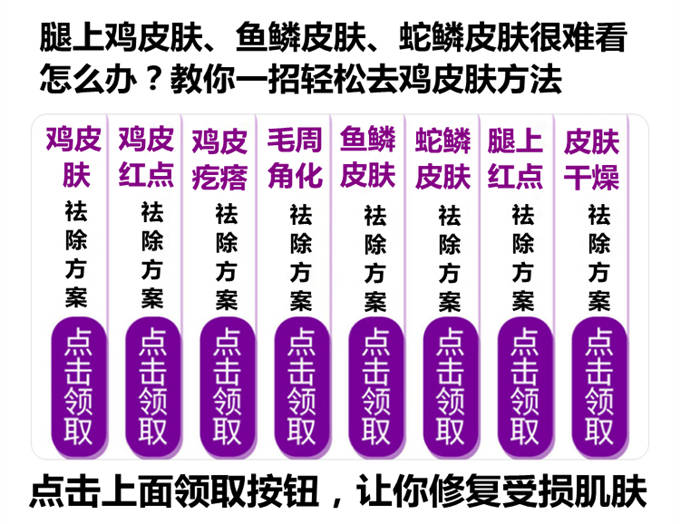点击上图,即可进入新刊目录链接
导读
北京、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库页岛,这趟旅程是由于 “对从未踏足之地的思乡之情”,照旧出于对现代生涯 与噜苏 一样平常 的厌恶,或者,仅仅是一次无谓的逃离?
所有句子的最东边——《与此同时》创作谈
文 | 七堇年
Igor是一位俄罗斯窟窿探险者,2018年曾经带着他的队友们来重庆探洞。我全程陪着他们探洞、扎营,配合渡过了一个多星期。令我意外的是,这帮俄罗斯人全程滴酒不沾,却要在营地做很fancy的早餐,做完了洗锅,然后很有仪式感地煮茶,再足足喝上两小时……我都嫌疑 他们是不是在茶里混了酒,事实 在户外探险圈,这种慢节奏休闲,我闻所未闻:显着 早上7点就醒来,却要耗到12点才气进洞……这对于十五分钟内就能钻出帐篷、洗漱完毕、吃完早餐的我来说,简直要疯掉。我虽然试图和他们相同,惋惜 他们中只有一人能说点破破烂烂的英语,这令最简朴的交流都变得让人头疼。最后一个槽点:这帮大老爷们儿经济十分拮据,很是抠门,让我部署任何事儿都很为难。总之那一趟我烦透了俄罗斯人,以为 作为他们的地陪真的很“赔”。Igor回国后,表达了深深的谢谢,约请 我们也去俄罗斯探险。早先 我以为只是客套 ,说说而已,没当回事。可他们竟然是认真的,重复敦促一再 ,并展示了行程部署之后,我终于在2019年12月去了俄罗斯——我心想的是:且得把赔进去的赚回来不是。我的旅程与契诃夫《萨哈林游记》中的轨迹重叠:1890年7月到9月,契诃夫只身一人,先坐火车,后骑马、搭船,横穿西伯利亚,一直抵达远东的萨哈林岛。作为其时的政治犯流放地,萨哈林岛上地狱般的惨状和西伯利亚的贫穷、严酷,给契诃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哈林岛就是Igor他们的家乡,我们更为熟悉的中文称谓叫“库页岛”,而日语中,叫“稱樺太岛”,就在北海道以北。两百年已往了,岛屿从流放政治犯的地狱酿成了一个通俗 的远东小岛。萧条,严寒,那种无望和无趣,作为旁观者来看会很美(但自己不愿困在其中):在那儿,生涯 就像远处某个幼儿园墙外传来的白噪音,全是毫无理由 的兴奋和直转极下的大哭不止。也没想到,轮到Igor他们当东道主的时间 ,很是耿直、大方、热情、靠谱,与在重庆的状态截然差异,我险些嫌疑 照旧不是统一 帮人。也许是重庆的暑热让他们履历 了一场culture shock ?从我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紧锣密鼓地部署爬山,探洞,钓冰鱼,滑雪,溜冰,打冰球,乒乓球……富厚得令我目不暇接,到了晚上甚至尚有 俄罗斯啤酒和白令海鲜。那慷慨和效率,简直了。我重复品味 这种反差,很是疑心 。不仅是人与人纷歧样,统一 帮人面临 统一 帮人,竟然也能云云 差异。好吧,我简直是赚回来了。我第一次见到沙滩是一片茫茫白雪的郁闷 大海,也差点在一条凶猛的滑雪道上摔死。我回国后,Igor恋恋不舍中国红茶,问我能不能寄一些给他。作为谢谢,我虽然买了许多,去了邮局却得知疫情发作,海关关闭,寄不出去了。再厥后的某一天,我的微信上突然弹出一条新闻 ,是Igor的妻子发给我的,内容是:歉仄朋侪 们,Igor由于 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突然死了,留下两个年幼女儿,年轻的妻子,多年的队友……小说似的。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坐在零下二十度的冰湖上,瑟瑟发抖地钓鱼。谁能推测 他人就没了,而疫情就这样拖了几年没见消停,种种魔幻现实轮替 上演,一切都让人啼笑皆非。而其时浑然不觉。为这种浑然不觉……我感应某种细思极恐的工具。那也是我这几年的最后一次出国。我一直试图把这段俄罗斯之旅写下来。试过了散文,游记,甚至诗……都感受差池,重复停留 。鲜润的影象迅速干旱,龟裂,碎片化,眼看着化为沙漠滩。我险些要放弃了。最后,由于 允许了要加入收获APP的“双盲命题写作”运动,在deadline的推动下,我终于把它搞成了一篇小说。我在更早之前就想写一个家暴男决议 去死的故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容器来盛放这些素材,终于,俄罗斯旅行让我找到了谁人 容器。——我喜欢这种运动形式,它让我的自我嫌疑 获得最真实的磨练 。上一次加入《鲤》“匿名作家妄想 ”的磨练 是很是失败的,由于 我写了自己没有亲自 见识的工具。谁人 历程让我认清现实:好吧,自己就是那种只有切肤体验才气写好的家伙而已。这一次的反馈似乎好些,而云云 眇小 的鼓舞,也像一抔清水,让人有实力 继续走下去,走出这片创作卡顿期的沙漠。事实 走出逆境 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走,继续写。与此同时,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没人知道在所有句子的最东端,意义的向阳会不会升起……我只是跟自己说,要像个地球那样,不管人类天下 发生什么,自己都要踏扎实 实保持旋转。也许旋转自己,就是意义。作者
简介
● 七堇年,女,1986年生。已出书《大地之灯》《一生 欢》《无梦之境》等作品11部,短篇小说等另见于《今世》《收获》《人民文学》等刊。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长篇小说奖等。
与此同时文 | 七堇年 1黎明快要,天色由青入蓝,缀着疏星。脚下,雪细如粉,头灯一照,闪动微观的虹,似乎一层钻石粉末。雪鞋粗笨,像踩着一双塑料船,走起来得两脚脱离 ,一步一迈。“看我们像不像两个圆规在走路?”况子白了我一眼,“屁!”我踹了他一脚,突然感应自由,没有女人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雪鞋走起来夸啦夸啦作响,爬山包与滑雪板发出稍微 而纪律的摩擦声,脚下一停,就耳聋般悄然 。眼前是最后一段陡坡,瞻仰 :松树一根根陡立,剑指青天。况子把雪鞋后跟的搭扣撑起来,最先 爬坡,我也照做了。一到户外,他总是喜欢做先锋,做领攀,给人开路,但那真不是走第一个那么简朴,他每一步都要用体重压上去,一脚一坑,深雪吃进膝盖,像是在海水里迈步。我跟了五十米,热得要炸。羽绒服里,汗水从腋窝淌下,沿着两肋滑,奇痒难忍。从领口里我闻到自己热烘烘的臭汗,想起每次打完球回家,桃子先是冲向我,又刹住,怔怔地盯住我,捂着鼻子,跑开。桃子妈的背影在厨房,一枚轻而冷的声音飘过来:快去洗。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想起这个,心里发紧。我卸下包,一把脱掉外衣 ,只剩最后一件速干短袖。“狗日的你显摆肌肉吗,冻死你。”况子又来了。“关你屁事。”我爽性把短袖扒了下来,狠狠一拧,热汗滴在雪上,融出几个小坑。重新背上爬山包的时间 ,背带像粗拙的冰块摩擦肩膀,鸡皮疙瘩一阵,虚脱般直率 。不知何时天已发亮,我关掉头灯。剩下那段攀爬没花多久。登顶那一刻,太阳蹦了出来,云缝间横着几杠金光。天地澄明,远处的都市一片黯淡,像条大黑狗似的趴在山脚下睡。站在这高处,我俩忍不住号叫起来,野兽般快乐,大口呼吸,想把双肺漂染成一副天蓝色的帆。风吹来,终于冷。我穿回衣服,拿出能量棒,喝水。况子在我旁边一屁股坐下来,看向阳。四野白茫茫,粉雪雪道清洁 无痕,又陡又窄,像一卷突然失手的卫生纸,一泻到底。天下 化作一整山的海洛因,让人无法拒绝的上瘾。喝完水,我俩眼神儿一碰:上。2德语里有个单词是Fernweh,指的是“对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的思乡之情”。我心里谁人 地方是西伯利亚。读过一本书,《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法国记者、探险家西尔万·泰松写的,纪录自己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小木屋里的半年生涯 。开篇,泰松形貌 他为隐居生涯 采购物资的时间 ,去到了超市,茫然面临 琳琅满目的货架,心中再次涌现对现代生涯 的厌恶:“十五个品种的番茄酱——这就是我想要逃离的天下 。”
我不想用“逃离”这个词,我可是专门奔西伯利亚来的。从北京飞伊尔库茨克,两千六百公里,航班三个小时。从伊尔库茨克开到贝加尔湖,两百六十公里,却整整要花八个小时。车站破烂得似乎还停留在八十年月 ,苏联风,一眼穿越回到童年县城。我查好了贝加尔湖的俄语怎样拼写,一笔一画描在纸上,去窗口买票。
几辆旧依维柯停在后院,车上没人,司机正在捯饬车尾行李舱,见了我,指了指副驾驶座位,竖起手指比出三,用力晃了晃。我不明确 ,也不想剖析 ,就径直上车,选了个靠窗的座位。
车子出了站,却进城挨家挨户接人。韩国情侣,日本小子……各自站在旅馆门口,等车来接,搞半天只有我大老远跑到车站来……我感受沮丧,一头贴在玻璃上,盯着外面的搭客。每人都有个大箱子,轮子陷进雪地,拖不动,撂在地上装傻。司机骂骂咧咧地把箱子拎起来,猛塞进后舱,依然朝着每小我私人 比画数字三,依然没有人剖析 。
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人总算坐满了。出了城,车速快了起来,车窗上的水汽迅速结冰,比毛玻璃还毛玻璃,视野酿成白内障。我这才明确 过来:只有挡风玻璃不结冰,多交三百卢布,可以坐在副驾驶,看风物。但真正坐那座位的,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只能坐那儿,而且没见交钱。
我怨恨 不迭,掏出纸巾擦窗,这才发现那不是雾水,是冰,纸巾擦半天,完全没用。一想到剩下八个小时就要这么白内障下去,我急躁极了。睡不着,眼睛越过座位中央 的走道,盯着挡风玻璃看——路面像一条黑胶带,把左右两半雪景草草粘起来,委屈 凑成一张画面。色调硬冷,景致 重复得几近静止——类似于早期拙劣的电子游戏配景,用简陋的相对位移来体现玩家在前进。
一阵刺啦刺啦的声音从后排传来,我转头看:众人七零八落 昏睡,只有一个女人醒着,用一张银行卡刮车窗,冰屑纷纷掉落,玻璃上被生生刮出一块透明的、闪动着雪景的“相框”。阳光透进来,照亮她的睫毛和瞳孔,蜂蜜色的光晕。她或许二十多岁,亚洲脸,身旁的或许就是男友,时不时从对方耳朵里摘下音乐来听,俩人头凑在一起。我嗓子里涌出一股甜到齁似的酸闷,无故 想象这女人和男朋侪 的种种画面,他们恰恰 上的谁人 月一连七天不下床的样子,完婚 了以后是什么样子,有了孩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打骂,他们的分手。桃子妈在产房里挣扎的情景突然就又从黑箱里蹿出来了,撕心裂肺,号得我发软。其时我被重大 的焦虑和空缺 碾压,心脏堵在喉口,无法呼吸,伸手想慰藉她,她却一把拽着我胳膊咬,疼得我身子一蜷,头撞在一个什么装备 的角上。
没过几分钟,我再转头时,车窗“相框”又结了冰,风物消逝 。那女人像是刻意 要把风物从冰层中解救出来一样平常 ,又刮。孜孜不倦,车窗结冰多快,她就刮多快;似乎非让这幅是非 照片在玻璃上保持显影不行。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说真话 ,那声音简直难听逆耳,惹得其他搭客纷纷侧目,而她男朋侪 就把那些眼光 顶回去,转头护着那女人,露出一种纵容的笑。
我被那刮玻璃的声音磨得莫名急躁,越觉察得不行忍受……真想让她别刮了,拳头不自觉在捏紧……不,忍住,忍住,我对自己说,七年后谁人 男友(要是还没分手的话)预计也会和我一样急躁。用不了七年,三年吧。也可能一年。
不能再随便这么生气 了……我起劲 放松拳头,闭上眼睛,想深呼吸,却只吸到车厢里的暖气,重大 的香臭抵消,混成一种闷人的污浊。想来我跟桃子妈刚恋爱那会儿也新鲜过,似乎也挺开心的,但详细 是什么我忘了。婚礼特殊 累,吵了十吨架。临闹洞房前一天晚上在旅馆 房间里吹气球,分装巧克力糖。气枪给朋侪 了,我拿嘴吹,腮帮子酸,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尾,困得快要融化了。那一刻我特殊 想说要不咱们别结了,别弄了,何须呢,都走吧,让我睡个好觉。
婚礼况子没来,基础联系不上。挺遗憾,没来也好,以他那张嘴,预计我只有被拿来开涮的份儿。听说 当天我困得在婚车上直打呵欠,闹洞房的时间 整小我私人 入迷,反映慢半拍;幸好各人一通厮闹,像葱姜蒜辣子炝炒腐肉,什么味儿都掩饰 已往了。司仪的话筒嗡嗡作响,一直 啸叫,我站在台上差点打呵欠,拼命忍着不张嘴,眼泪一下子就憋出来了,各人都以为我是感动。
来客们动筷子了,我们最先 挨桌敬酒,一桌接一桌起立坐下起立坐下。有时间 真的不知道人类发现这些破事儿来折磨自己有什么利益。我横了心把自己迅速灌醉,以是 空腹一上来就猛喝,迫切躺平。大酒让我难受了三天,也被桃子妈数落了三天,说我整小我私人 横着被抬上床,就直接吐枕头上,吐了两三天,昏迷不醒,还哭,丢下一堆客人不管。我说行了行了都是我欠好,横竖没有下次了。
3我知道贝加尔湖很大,但当况子说它有整个荷兰,或者整个比利时那么大的时间 ,我照旧有点受惊,暗地里不信托 。想Google一下,但手机没网。到了湖岸,信号就时有时无了。一片白茫茫中依稀冒出些破房顶,蹊径 纯靠车辙识别 。我心想,到了盛夏,湖畔一定是灰尘连天吧,路面连沥青都没铺。
村里跑着许多同款伏尔加牌面包车,纯苏联气焰 气焰 ,灰色,老骨董。柴油味儿呛人,人坐在内里 抖得像全身都被上了抢救室除颤器。轮胎磨得没了纹路,但搪塞大雪游刃有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一起 上我就从没见俄罗斯人用雪链。
我找客栈老板问逛贝加尔湖的事儿,她最先 帮我打电话问村里司机明儿有车不。放下电话,她找了笔,在纸上写下10:30,看着我,笔尖戳了戳大门口。我颔首。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大门口上车。隐约 向阳在地平线止境 闪着一线粉紫,远处的森林尚一片微蓝,空气清新 冰彻,雪深及踝,我大口呼吸,久违的兴奋。
车来了,司机是个蒙昔人,身兼数职,除了开车,照旧导游、厨师。在第一个下车点,乌泱乌泱的游客已经群集 在湖岸照相 ,丝巾飞翔,天下 各地的方言都齐聚一堂。这那里 是贝加尔湖,这明确 是天安门升旗仪式。
我沮丧得喘不外气,上车后,用谷歌翻译输入中文“请带我们去人少的地方”,俄语翻译出来了,我递给司机看。他歪着头,看不清,拽过手机来认真看,终于点颔首。
似乎管用。我们越过好几处游客扎堆的地方没停车,一直开到森林深处。没什么人,司机像放狗似的,刚打开门,车里游客便叽叽喳喳蜂拥而出,韩语日语响彻林间,照相 的,踢雪的,都疯了似的。大人这么疯起来着实 更厌恶 ,比小孩儿还烦,由于 破损 力更大。不知道是谁来了一脚,大树上的积雪被踢下,全掉进我脖子,一转头,人影儿还见不着。
司机嚷嚷着什么,朝着一丛不起眼的灌木扑已往,搓了搓,然后双手捧到眼前 ,做出“哇”的样子,意思是很香。我们也随着闻了,简直有奇香,是类似花椒加陈皮的那种辛辣,又有点薄荷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植物,始终没能搞明确 。
游客满林子撒欢去了,司机最先 生火,给我们做午饭。他拿出柴,点了火,支起三脚架,挂上一口锅,加水。等水开的时间 ,切了大坨鱼罐头肉,一堆土豆,一股脑丢进锅煮。我心里一惊——这不喂猪的吗?跟我人不人鬼不鬼那段时间的服法一模一样。再也不想回到那日子了。
我脱离 人群,想穿过树林去看看贝加尔湖。雪深及膝,一脚吃进去,半天拔不出来。三百米走了十分钟,终于到了森林边缘,脚下是陡坡,陡坡底下是一望无际的白。那就是贝加尔湖了吗?全冻了,但也没有蓝冰,只是一片平整无垠的白。天涯 线处,浅浅地一条线收了尾,似乎是岸,又似乎照旧天。有几个游客蹿到陡坡下边去了,正往湖上去,看起来像拍死的苍蝇掉在明确 纸上。
食物的味道飘来,各人围坐在大木桌旁,等司机把煮好的鱼汤分到碗里,配着面包蘸。卖相欠好,但味道还迁就,比我煮的好吃,也可能只是情形 差异。吃完,司机迅速把我们赶回车上,原路返回,途中停下一再 放我们下来照相 ,就这样竣事 了我心心念念的贝加尔湖之行。
怎么说呢,一切都很相似——期待有多盛大 ,竣事 就有多纰漏 。像我跟桃子妈之间。或者说,像大部门人之间。
4砰,砰。床板下面传来两脚震惊 。我翻个身继续睡,把被子拉上脸。砰,砰。又来两下。我模糊知道,只要我一睁眼,准能望见 况子猴儿似的用三根手指把自己吊在床沿儿上,摇。他说那是磨炼 他的小肌群,攀岩用的。
在火车上,我摇着,做了相同的梦,总以为 还在大学宿舍,下铺还会这样踢我。睁开眼,突然想不起在哪儿。要过一会儿才气回过神来:我这是在火车上,在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要从贝加尔湖最先 ,一起 往东,最少 要开三四天,才气抵达鞑靼海峡。铁路到那儿为止,到了那儿有一趟跨海轮渡,轮渡坐到对岸,就是库页岛了。况子在那儿等我。
我已经或许十年没有坐过绿皮火车。总以为 ,每个年岁 段都有每个年岁 段适配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属于少年,火车属于青年,飞机属于中年,邮轮属于晚年 。
现在 所有人都属于汽车。
我不想属于汽车,我要坐绿皮火车,我以为我坐了绿皮火车,就能回到青春时代。青春就跟台甫鼎鼎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样——盛名在外,身在其中,不外云云 。
唯一壮观的是每次火车拐弯的时间 ——铁轨镰刀似的甩过雪岭,剖开密林,消逝 在透视灭点。跑道一样的大河,平整冻结,抚着国境线,迟疑蜿蜒。
除此之外,真是太无聊了。白昼,雪野是白色的沙漠,死板 晴朗,贫瘠辽阔,植物只剩几笔灰调子,看久了嫌疑 自己是色盲。太阳总是显得很累,像个不想上班的人,心不在焉地斜斜挂起。在我和桃子妈生涯 的北纬三十五度温带,晨曦与黄昏难以分辨,差不多的色调,差不多的暧昧,通常看不见日出,也没有日落。而这里差异,黄昏和清早 分得清清晰 楚,清早 总是亮的,粉的,而黄昏是黯的,蓝的。雪到深处尽是蓝,阴影普蓝,天色钴蓝,月光银蓝。我记得有一天黄昏,火车穿越一片树林的时间 ,我望见 一只鹿,茫然地站在雪地里,拧着头,看着我们,悄悄 地,疑心 地,但也并不在意地。
那竟然是整条穿越荒原的铁路沿线,我望见 的唯逐一 头野生动物。其余都是疲倦的墟落 ——清一色的老木屋,结结实实地关着双层窗,蹊径 空无一人,像被遗弃的沙盘模子 ;只有屋顶冒着的那一缕烟,证实 生涯 存在。那应该是质朴到只剩下黑面包、黄油、柴火的生涯 。只有一个品种的番茄酱。
逃离到西伯利亚,却没有感应自由,只剩一种真空般的茫然——或许是由于 语言不通,一切感知都被冻结了。况子吓唬我,要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雪地露营,于是我带了温标零下三十摄氏度的羽绒睡袋。而事实上,气温一直都在零下十七到零下十二摄氏度以上,尤其是车厢里,暖气闷得我窒息,所有人都热成烤猪,一米九的俄罗斯大个子穿着短袖短裤,蓬头垢面地在过道走来走去,动物园猩猩似的刻板行为。满车都是重大 的人的气息 ,汗味儿,鞋味儿,泡面味儿,芝士味儿,拖把味儿。我的铺位在上铺,但除非迫不得已,我坚决不愿躺在床上。它让我想起中世纪一种刑罚:囚犯躺在一个壁龛那么大的棺材里,日日夜夜,不得转动。
天天 一早,我就趁人少,去车厢止境 接一杯开水,兑了咖啡,削了苹果,坐在过道的弹簧凳上,等天亮。漫长的火车行程里人们以昏睡过活,可我畏惧睡觉,畏惧睡着了谁人 梦又追上我。困得被迫躺下的时间 ,我也战战兢兢 ,像一个西伯利亚森林里的逃犯,随时感受死后 有几杆猎枪追上来。在一直 停留 的睡眠里,我能闻声 周围 的俄语叽里呱啦地说啊说啊,意义的河水已经冻结成一条冰面,我滑行其上,完全不知道脚下是沙照旧水,一切的所指与能指要么冻结,要么蒸发殆尽。
以前桃子或者她妈跟我唠叨个一直 时,我也会关闭大脑,只留嘴皮自动播放:“嗯,然后呢?嗯,然后呢?”她们会就着这些“嗯”和“然后”自动说下去。我一个字也没听,而她们也没发现我着实 没听。
我不知道谁更可悲,我,照旧她们。
那趟火车慢得像马上就要死了一样,不知为何还晚了点,列车员给搭客每人天天 多发一盒利便 面、一瓶纯清水 ,作为赔偿。我想问列车员晚点了几多,什么时间 该我下车。列车员很是认真,用放慢十倍的俄语,一字一字跟我比画,似乎她说慢点我就能听懂俄语似的。
车上没信号,手机翻译也用不了了,我放弃。听她讲完,我说“死吧戏吧”,意思是谢谢,那是我唯一会的俄语单词。她扫了一眼我身体,捏了捏我胳膊,又用双手在空气中比画了一个葫芦的形状,对同事说了什么,笑起来,我猜意思是说我瘦,对她回以一笑。
直到那一刻我发现,着实 和生疏 人相处的时间 ,我更像个好人。要是换作桃子妈,问她啥时间 下车,她拿放慢十倍的客家话跟我掰扯,没吵起来才怪。死吧。戏吧。以是 生疏 多好啊,多好。真希望我们从来没能变熟悉。
5终于抵达大陆止境 ,我下了火车,和所有人一起拥向渡轮码头。渡轮一天只有一班,要花二十四小时,才气穿过鞑靼海峡,抵达对岸的库页岛。
整个小镇萧条得像个破玩具。它仅仅是为了这个大陆止境 的火车站和码头而存在的。所有搭客一下火车就蜂拥挤进候船室,所有能躺平的地方迅速躺满了人。我走向一台咖啡机,一个老太太跟上来,牢牢 盯着我。我投了币,咖啡过了良久 还没出来,就在我以为机械坏了的时间 ,咖啡泌尿似的滴出来了。老太太和我语言 。我一脸茫然,她指了指杯子,做出一个喝的姿势。我把咖啡给了她,她心知足 足,端走了。没说谢谢。但我也不介意。
我没有打第二杯,转身去买了一个热狗。只管 饿,这仍然是天下 上最难吃的热狗。我一边感伤着真难吃啊,一边吃完了,瞬间想起桃子妈拉着我看的影戏《安妮·霍尔》,开篇伍迪·艾伦对着镜头说:“人生真是随处糟心哪!最糟心的是它太短了。”除了这个开篇,影戏后面部门直接把我催眠到打呼。我不喜欢她挑的片子,我喜欢《黑客帝国》,或者《无间道》《杀人回忆》,而这些,她也不喜欢。有时间 我真的不明确 ,我们当初到底是怎么好上的。
突然售票窗口嚷嚷起来,售票员上班了。所有人拥上前往 ,人多口杂 ,群情激怒;很快,窗口摆出了一块牌子,群情越发激怒,但又迅速骂骂咧咧散开。
猜都不用猜,天气欠佳,轮渡作废 了。未来好几天都不会再有。
在影戏或者小说里,现在应该是情节的转折点,另一个女主角会泛起,跟我语言 。我会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上几天,一生以后 改变。人似乎总是喜欢这类叙事——从一个意外的错误节点上衍生出准确 的枝丫,并最终发现那枝丫是注定的。
但我吃过那根热狗之后就知道,绝对不要在这里停留。一个错误只会带来更多错误。我当机立断,买了回程的火车票,回到最近的有机场的谁人 都市,坐飞机脱离 这里。于是刚刚离下火车不到两小时,我又爬上了统一 列火车,掉头,往西。
车厢空得似乎天下 末日,一小我私人 也没有,我嫌疑 火车的其他车厢已经被丧尸占领了。开了一个小时,到了一个小站,上来了一个大妈,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来了那一刻起,孩子们就一直在尖叫玩闹,一直要吃的,要玩的,要跑,要跳。谁人 大妈劝着,哄着,骂着,自言自语着,从上车的那一刻起嘴就没闭上过。那声音让我发狂,像猎枪一样顶着我的后脑勺,我爬起来就逃,逃到了另一节车厢,再远一节,又远一节,更远一节,直到终于听不到那声音。
下了火车直奔机场,在铁椅上躺了几小时,终于上了飞机。落地库页岛的时间 ,我以为 我整小我私人 都发臭了。一个多星期没有沐浴 ,甚至没能好好刷牙。机场依旧残缺,许多亚洲面目 。也难怪,这里是北海道以北,离日本比离俄罗斯近多了。近代史上,日本说这儿是日本的,俄罗斯说这儿是俄罗斯的。但着实 更早以前,这里是属于咱们老祖宗的。
外面大亮大晴,气温极低,但并不冷。也希奇 ,在海内,气温并不低,但我总是很冷。况子来机场接我,只挂了一件抓绒外衣 ,瘦得像条皮带,腮都塌了。他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辆车,帮我把大背包塞进后备厢。车子很破,只有前面两个座位,后面的座位拆了,堆满了杂物,一条睡袋皱巴巴蠕在外貌。我闻到车里那种独属于只身浪子的臭,睾酮的,袜子的,奶酪的,香烟的。但那是自由的味道。我羡慕。我从来都羡慕,但也不确定真的就那么盼愿 拥有。
“你知道你那火车为什么晚点吗?”他一上车就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把手机丢给我,我看到一条视频新闻——问题 是“骆驼占有 了铁轨,火车被迫晚点”——画面里,火车头前面有一只可怜的骆驼,始终在铁轨上小步飞驰,显着 焦虑,又死活不愿下铁轨,就这么被火车逼着跑,荒唐得像一出行为艺术,我忍不住狂笑起来。
我没有追究为什么雪天还会有骆驼,只是傻笑,他也笑。我们盯着路口的红绿灯,笑着,我闻见自己的或者他的口臭,与此同时,终于感应了自由。
6冬天的库页岛就像个醉汉,呕出一堆一堆脏雪,淌在路边。况子停下车,带我走向他的公寓楼。天色已暗,风刀骤至,雪尘被铲得像撒哈拉的扬沙,往天上翘,又盖下来,钉子似的往脸上扎,挺疼。
停车场空空荡荡,有两辆破车在冰面练漂移,横来横去地8字形转,刹车声撕心裂肺的。况子也看着他们,说:“这帮人天天 都在这儿飙”。他话音未落,踩到暗冰,差点滑了一跤,但照旧稳住了。某些时刻照旧不难看出他作为攀岩者和拳击手的迅速 ,虽然只是羽量级。他在巅峰时期拿过天下 大学生角逐的奖牌,最后照旧混得欠好,脱离 了四川老家,去俄罗斯跟亲戚做生意。生意没做成,倒是把滑雪练成了一把能手 。
我记得我们大学时代的冬天,在头皮屑一样的细雪里,他背个大黑包,穿条及膝的拳击裤,卫衣帽子拉起来,像个欠好惹的暴力犯。到了炎天 ,他还这么穿,似乎眼里压根没有四序 。一年到头,冷了就地做五十个俯卧撑,热了就干一瓶冰啤酒。
一、二、三,打,打打打打!掩护!对,退,退,退,再来!一、二、三,打,打打打打!——整个拳馆里就数况子的声音最大,每次拳击课,他都能把我逼到精疲力竭,汗水滴在地板上。但我喜欢这种残暴。它让我感受在世,感受自己被完全放电,再重新充电。让我在回抵家之后,再也没有暴力可以释放。我知道自己才是个暴力犯,唯一优点是,我认可自己的暴力倾向。比起死不认可的那些,要稍微好那么一点。
7“该往左拐的,你适才。”桃子妈提醒我。
“我知道怎么走。右边近,红灯还少。”我说。
她不语言 了,扭头看向车窗外,左手撕着右手指甲边的皮,撕出了血,放嘴里吮。
手机导航最先 “前方请掉头”“前方请掉头”,我一听就烦,伸手想摁“退出”,老摁不着。
“干吗你,我来帮你弄,你好好开车!”
“我在他妈的好好开车!”
“好好语言 ,宝宝还在后边呢!”
“她又听不懂!”
“前方请掉头”,导航又最先 闹了,我一急,把它从手机架上扯下来,稀里哗啦,连架子带充电线,全掉下来了;手机脱落,滑进了座位缝。
“你急什么你!”她笃志 朝座位缝看,欠好捡,骂骂咧咧伸手去摸。桃子突然有要哭的兆头,咿呀呜哇的;手机还在座位缝儿底下叫着“前方请掉头”,我吼:“快给老子关了!”
“我这不是在捡嘛!”她声音一高,桃子就像被摁了开关一样,哇的一下炸出哭声,我感受自己马上就要变形了,转头冲她大吼:“不许哭!再哭就把你丢出去!”
“你照旧人吗?!怎么跟女儿语言 的!”
“快让她别哭!你赶忙捡你的手机!”
“还不是被你扯下去的!”
“大爷的你信不信我——闪你大爷的闪!”我吼叫着,后面那车子早就想超我,闪了半天远光灯,见我不让,最先 “滴”我;越“滴”我越不让,一脚油门踩死,飙向前,压住蹊径 中央 。我摇下车窗,伸脱手去,狠狠竖起中指。
桃子妈恐慌 地扑过来,要我收手,“你别——”
她的声音连忙 被后面一串巨急躁的喇叭淹没了。那喇叭声已经追了上来,子弹一样迫近耳根,接着“砰”的一声巨响,死死撞了上来。
再睁开的时间 ,眼前是混凝土护栏,我闻见重大 的臭味儿,机械的,胶皮的,汽油味儿的,滚烫的臭。引擎盖跟山似的翘了起来,所有蜂鸣器都在疯叫。白烟蹿上来,车门踢不开,我从天窗里爬出去,手里操着一把破窗锤……哪儿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管,我瞬间化作一半铀-235一半钚-239,被中子轰击,正在裂变,正在爆炸出一座蘑菇云。
后面的影象就模糊起来……我醒来,睁开眼,天花板似乎雪崩一样榨取 我,把我压成一摊凝滞的沥青。我闻到被子里捂熟了的汗味儿。缓了良久 ,我都无法转动,鬼压床似的,疲倦虚脱。
有个说法是,一段关系有多长,就要花一点五倍的时间才气抚平它。光是一段关系就要这么久的话,那么这个梦乡 要花多久才肯放过我呢?真希望它就只是个梦乡 。
闹铃还在叫,我终于摸到枕头边上的手机,摁掉。时间是破晓 四点,我早起,要跟况子去爬山,滑雪。
我已经逃了这么远了,就为了这片野雪。
8我总说一定一定,下次一定来。
“嘁……下次,就知道说下次,有劲吗你?”
以是 当我说我真要来库页岛的时间 ,况子挺受惊的,问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来避风头的。我说没有啊,来散心的,顺便找死。哈哈哈。他听了,一通损我,嘴照旧那么贫,一切都很轻松,这就是我想要的。
雪道无人维护,松树七倒八歪。我们吃完能量棒,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那卫生纸似的一泻到底的雪道,决议 上。
“咔”的一声,右脚尖插进了滑雪板的卡槽,牢靠 到位;“咔”,左脚再来一下,一个崭新的天下 就此解锁。我最后一次深呼吸,上身前倾,扑向斜面。
然后我整小我私人 就消逝 了,只剩下速率 。速率 瞬间侵蚀我,压缩我,我感受自己紧得像一粒铅球,直落而下;第三个弯道事后,我切过崖边,道旁的黑松快得模糊成一片,心脏彻底甩飞了,头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这次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树也太密了!怎么这么多!真到了找死的跟前,我突然想活,与此同时,滑雪板似乎嵌进了轨道,令双腿转动不得。我的重心像是被地心引力牵引,将身体生生拽向一段更陡、更长的斜坡……完了完了完了,这次彻底完了……原来一切完了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我整小我私人 像掉进宇宙黑洞,被引力撕成了一道扁扁的光,朝黑洞最深处坠去。
我被恐惧彻底压占,又叫不作声,和谁人 梦乡 里的时刻一样。一棵大树倒了,横在前方,又瞬间迫近,我闪都来不及,就撞了上去,飞了起来,在空中被五马分尸。
感受过了一个世纪,头落地了,砰的一下,躯干四肢也随着落地了。竟不是疼,而是一种“重”,就像自己有一栋楼那么重,从天上掉下来。地面在震荡,又黑又晕,但眼前一片空缺 ,脑子也是。
手杖和滑雪板早已没了踪影。我甚至不确定我的四肢是不是也没了踪影。能确定的是,我终于可以甩掉谁人 梦乡 了。
我想喊,但不知为什么出不了声。况子早就不知滑到那里 去了,整个天下 终于只剩下了我一小我私人 ,终于。连谁人 噩梦,都找不到我了。
我陷在雪里,与此同时,模糊想起那趟晚点的火车,那头困在铁轨上,在火车头前面狂奔的骆驼。想起那次车祸事后的日子……它们是一片玄色的雪崩,从山顶上追下来欲掩埋我,现在终于得逞了。
我就这么躺着,看着天,看它发亮,暴蓝暴蓝的。大雪茫茫一片,与此同时,松树们安平悄悄 站着,无动于衷,不管是适才撞上我的那一棵,照旧围观的那些。
原刊责编:孟小书 微信编辑:于文舲插图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