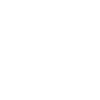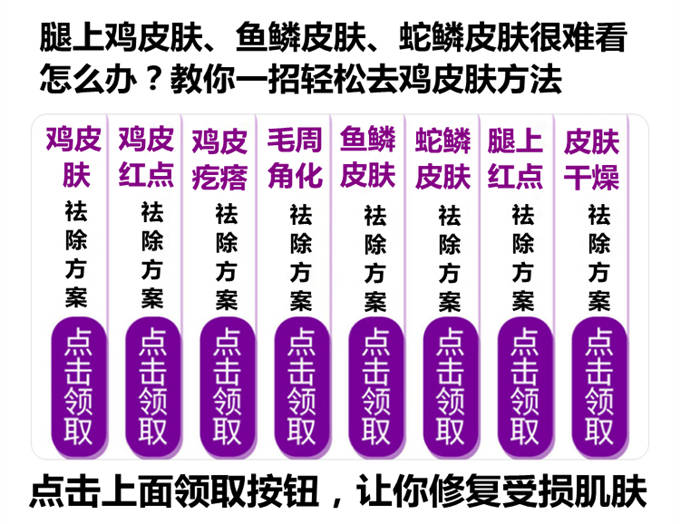我一度桃子过敏,只要摸一下桃子,老半天都全身 刺痒难耐。

着实 我小时间 ,可喜欢桃子,尤其是童年,影象里的那棵弯弯的桃树。
它长在韦曲原上,几孔通俗 的土窑前,而窑洞里,借居着姨妈一家人。
每逢暑假,我总是一头痱子,只要住进姨妈家的窑洞里,不出三五天,痱子痊愈。窑洞在夏日 ,自然 的纳凉避暑胜地。晚上,我和几个表哥,在原塄上,拾掇一块地方,铺上竹席,居高临下,吹着凉风,看着一清二楚 的万家灯火,感受惬意极了。
那时间 食物缺少 ,各人海聊得饿了。由我认真 ,像贼一样,爬上那棵被桃子压弯了腰的桃树上,摘下七八个桃子,用衣服兜着,带给大伙儿。旱塬上,水很是名贵,基本不需冲洗,直接薅一把草,擦一擦桃毛,就咔嚓咔嚓地啃开了。可是 嘴瘾一过,纷歧会儿,就感受全身 不自在,桃毛搞得全身 刺痒,着实不惬意 。可是 痛且快乐着,直到聊累了,鼾声此起彼伏。
后三更 ,起露了,我们几个,冷得抖抖索索地,纷纷钻进窑洞里。
那时间 ,姨妈家也不宽裕,天天 早上,白面糊糊拌汤,不带一腥荤。菜就是凉拌茄子。今天是生拌茄子,明天是烧拌茄子。特殊 说下烧茄子,这个做法奇异 :将完整的茄子,埋进灶火的灰烬里,饭熟时,把烧得黑兮兮茄子,弄出来,剥了皮,撕下白丝丝的茄肉,挤捏出水,放了蒜末、盐和醋,端上桌,就可以开吃。
中午的饭,就是稀汤面,人基本吃不饱,不外难不倒我们这群小子。饿了,不是在原上摘野枣,就是吃桃子果腹。虽然,我照旧喜欢桃子。一次吃两三个,直到肚子撑撑的。
姨妈家有七个孩子,刚凑够一波金刚葫芦娃。不外前面的,立室的立室,出嫁的出嫁,就剩她的最爱,也就是家中的老幺,名字叫阿锁。最小的儿子险些是她的所有 ,从小娇生惯养,失事肇事的,她没少给左邻右舍,谢罪 致歉。
穷人苦命 ,姨伯六十岁时,就早早地走了,留下姨妈,日子依旧拮据。这时间 ,阿锁哥,初中没结业,就由于 砸课堂 玻璃,和同砚 打架,被开除了。
姨妈找校长,让表哥转学,可是没几个月,又是打架斗殴,这次,她彻底地失望了,表哥就成了社会闲人。
姨妈担忧表哥闲出了事,让他继续了姨夫的衣钵,在杜曲街道,逢集买菜和水果,可是 好景不长,又由于 和偕行 发生争执,打架后,被拘留。
姨妈奔走相告,花钱把人保出来。最后不知道听谁说的:家宅不安宁,就是由于 门前的桃树引来的祸。听说 桃树上住着gui母,而且桃,谐音“逃”,“淘”,前者是逃亡,后者是把钱财福气纷纷淘尽。败落。
突然之间,那棵年年挂果累累,被压弯了腰的桃树,就无辜地背了锅。似乎姨妈家的一切不幸、不顺,都是这棵桃树惹的祸。
在昔时 的冬季,也就是表哥阿锁二进局子的时间 ,姨妈终于下定狠心,把那老碗口粗的桃树,叫人劈了烧柴火。
那棵桃树没了,我也上初中了,平时也很少再去姨妈家了。听说表哥阿锁,放出去不久,就加入了当地一个帮会。事发后,在被警员 羁押的半道上,借上茅厕之机,翻墙逃了。
姨妈似乎一夜之间老了许多,她心不宽,整日郁郁寡欢。最后,被我母亲接到我家里,暂住时日。
她天天 像个祥林嫂一样,对我总是叨唠着自己的不幸。我那时不懂事,也不明确 这些,我总是不耐心 的,捏词 躲得远远的。她时常独自一人,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最后见到姨妈时,我已经上高中,她见了我,依旧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只是这时间 ,她更是语无伦次。我也不时地嗯、啊地应付着。可是 ,刚过一会功夫,她再遇见我时,就叫不上我的名字了。
在熬到六十九岁的时间 ,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直到此时,她娇生惯养的宝物儿子阿锁,还蹲在牢里。最后,她彻底地,没见上自己儿子一面,也不知道她临终,是带着多大的遗憾和怨恨 ,尚有 那种为人母的绝望和无奈,咽下了最后的一口吻 。
一年后,听说那几孔窑洞,年久失修,垮塌了,那棵被砍了的桃树,不知道它的根,有没有在世,横竖,我是再也没有去过。只是每年桃子熟时,我可能会想起,那棵弯弯的桃树。
再厥后,我立室立业,儿时的影象,越来越模糊,那棵桃树,在我的梦里,似乎再也没有泛起过。
现在 ,桃子熟时,我却很少再吃桃子。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碰桃子,全身 就起鸡皮疙瘩。厥后生长到,只要我看到桃子,那种刺痒的感受,令我格外的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