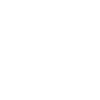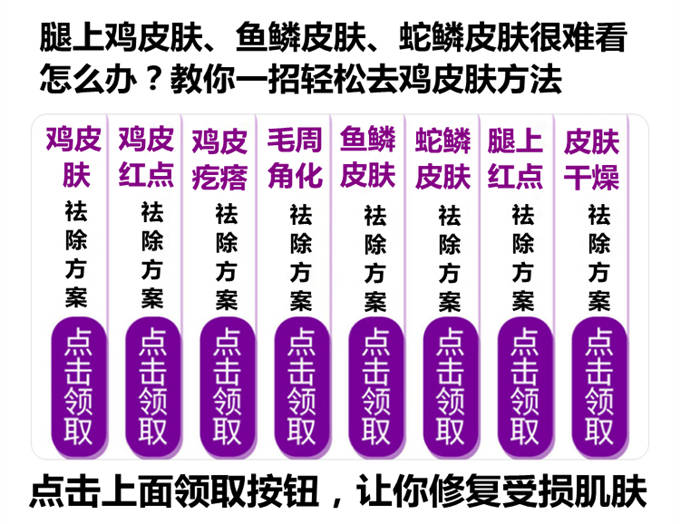时间:2015年8月20-8月25日
所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顿涅茨克市机场以西一公里的佩斯基(Pisky)镇
项目:乌克兰国防部随军记者项目(Embedded Journalists)

内容:在乌克兰政府军93旅位于佩斯基的哨所驻点,与士兵生涯 在一起。
陪同:乌军第93旅民事部翻译科斯佳,波兰记者沃伊季克
装备:单反,小DV,英制凯夫拉头盔,乌克兰制防弹衣
证件:护照,乌反恐新闻中央 签发的记者证,战地记者保险
一.第93旅指挥所
刚刚到达第93旅指挥所一个小时,我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Jackie”。来自哈尔科夫的阿马拉大尉用蹩脚的英语问我的名字。还没有等到回覆,他条件反射般冒出一个词:“Jackie Chan(成龙)?”
周围的武士 们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顿巴斯的夏夜里,无聊的武士 们聚在简陋的小木屋里喝着茶,开着种种各样的玩笑打发时光。这里距离前线足足有10公里,夜里清静 得让人想念多数会的疯狂。在死后 就是人们的清静 生涯 :有电视,有网络,有宠物。乌克兰国防部部署的93旅新闻官亚历山大·维兹金还会告诉你:“这里有妈妈。”
亚历山大的母亲住在30公里外的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是我从基辅乘坐火车向东的终点。
从基辅来的快车经由 6小时零20分钟,最高时速160公里的奔忙,先抵达克拉玛托尔斯克。这是2014年乌克兰东部武装与政府军首次发作冲突的都市。它的街道破旧不堪,异常清静 ,似乎还停留在苏联时代。
火车继续向东南开,到达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一年多以前,火车的终点站原来是更远处的顿涅茨克。可是 现在它落在东部武装手里。顿涅茨克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铁路客运中止 了。
这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是好事儿。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下火车,连忙 有一群当地人围上来,嘴里重复着三个简朴的英语单词:“记者”、“顿涅茨克”、“的士”——在已往一年里,不知道有几多记者从这个小站下来。一些出租车司机使用 自己有顿涅茨克身份证的时机,穿过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武装的封锁线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把记者带回自己的都市。在2014年,一个单程就可以赚到100美元。
不外,今天他们注定没法从我身上赚到钱。在车站期待了一个小时之后,亚历山大·维兹金开着一辆涂着迷彩的日产皮卡飞驰而至。皮卡货箱里装满瓶装水。他诠释 说,这是给驻地武士 们的饮用水。车厢后座里放满了种种面包、薄饼、肉饼和鸡蛋。这是亚历山大的妈妈给他和他的战友们改善的伙食。
皮卡追风逐电地跑起来,穿过广袤的南乌克兰大草原。蓝天下面要么是无边无涯 的向日葵地,要么就是枯黄的蒿草,蹊径 双方 是高峻粗壮的白杨树。蹊径 破旧,车道忙碌 ,从卡车到苏联时期的拉达小汽车,什么都有。若是 不算路上需要经由 三道乌军检查站,以及望见 两辆伞兵战车飞驰而过,险些就可以得出一个印象:这里基础没有什么战争。
继续往南走,行车最先 希罕 。皮卡从公路上下来,来到一处丘陵的反斜面,情形 最先 差异。亚历山大嘱咐我,驻地里不许照相 和摄像。在过了第四道检查站之后,就可以望见 披着伪装网的重型卡车,以及挎着枪站在卡车旁眼色阴森 的士兵。树林里稀稀落落地挂着种种伪装网,掩饰 着下面木头和砖墙搭建的各个遮蔽 部。这里是乌克兰国防军第93旅的指挥部。
亚历山大所在的第93旅民事部所在的遮蔽 部有三进。拐进去之后,雪亮的灯光下是第一进。中央 用弹药箱架着一块木板作为桌子,上面零琐屑 碎地堆着一大堆文件,条记本电脑,打印机,显示器。桌子一侧放着电话等通讯设施,另外一侧则铺着木板,上面搁着睡袋,看起来是两小我私人 头对头睡的床铺。“床铺”下端放着种种武士 的琐屑 :头盔、防弹衣、子弹带、背包、水壶、电筒。墙上的挂架上挂着种种衣服。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墙角搁着一把AK-74自动步枪。
步枪在这里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厥后发现,在第二进的崎岖床床架上,同样绝不掩饰地挂着几把AK-74自动步枪。我睡在第三进的上铺,脑壳 后面放着一把Ak-74。早晨起来,发现Ak-74下面还压着一把压满子弹的马卡罗夫手枪。枪口正对着我的脑壳 。
进收支 出的武士 们,腰上或者大腿上都挂着手枪,有趣的是。他们腰上挂着的刀却不是步枪刺刀,而是什么七零八落 的刀(也许匕首越发准确一点)都有。部署我住宿的科斯佳腰上挂着的刀还赫然写着“中国制造”。
科斯佳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基辅人。到了驻地后,他灌了我一肚子茶——战时军队禁酒,连啤酒也不许喝,科斯佳几多感应有点遗憾。部署住宿并不算难题 ,我这一天晚上成为了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夜里很是冷。”他说,然后递过来一盏头灯,告诉我怎样 如厕,就是说,小问题,朝路边沟里解决。大问题,请他老人家带队,告诉你上哪儿攒着。
想要把这几句话用英语向我诠释 清晰 似乎很难。科斯佳憋了半天也想不出“大号”和“小号”怎么说,又引来各人哈哈大笑,似乎任何一句话都市引爆大笑一样。亚历山大说,当我们很是畏惧的时间 ,就想出些可笑的事情让自己发笑。他很正经地问我:“你们中国人岂非 一点诙谐感都没有吗?”
这里每小我私人 都在用自己能够想出的英语单词与我谈天 ,主要的话题是北京,基辅,莫斯科。阿马拉大尉曾经在塞瓦斯托波尔服役。科斯佳的妻子是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人。一提及 克里米亚,两人都摇头说,哎呀,我们回不去啦。
隐约 约约的担忧从他们的眉头上展现出来。“8月24日是乌克兰自力 日。听说 东部的敌人会大打脱手。”一个没有说姓名的大尉在旁边说道。另外一位则增补说:“他们一天到晚打冷枪,用迫击炮打冷炮。”
“望见 那条狗了吗?它叫爱丽莎,”科斯佳说。这条德国黑背正在舔着盘子。科斯佳使劲拍了一下手,爱丽莎连忙 神经质地往后一跳,扭着头左看右看。“今年它在巡逻的时间 遭遇炮击,给吓出误差 来了。”
“佩斯基一带最近打得相当热闹。明天我带你去佩斯基。你准备好了吗?”科斯佳仰面 问我。
这个提醒让我想起了芬兰记者尼娜。昨天在乌国防部信息局才刚刚熟悉 她。信息局副局长把前线的情形 说得极为危险。尼娜于是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遇到炮击要赶忙躺在地上,而且要并拢两条腿。
我问为什么。尼娜突然放声大笑:“这样你才气保住你的蛋蛋!”
也许,这就是在心里畏惧的时间 所必须的诙谐吧!
黄昏时分,也许是四点半到六点之间,东边传来麋集 的枪声。可以听识趣枪有节奏所在射,显然射手是个内行 。种种枪声之间,时不时夹杂着霹雳 的爆炸声,间或有更沉闷的爆炸。厥后我才知道,前者是榴弹发射器打出来的榴弹爆炸声。这是一种让人防不胜防的轻武器,杀伤力相当于手榴弹。沉闷的爆炸声是82毫米口径迫击炮干的。
枪声迫近的时间 ,我们正在从西向东的一条路上,准备回到第93旅喀尔巴阡自愿 连的哨所。位置很倒霉,背后就是斜阳 ,敌人的偷袭 手可以在徐徐柔和的光线中看到我们的影子,由于逆光的缘故原由 ,我可以保证他们一定 看不清我的防弹衣前贴的蓝底白字的“PRESS”。另外,由于林木茂密,许多时间 对方只是举行 盲射,把12.7毫米口径重机枪用45度角扫射。子弹落到谁的身上,完全看各自人品。
凭证 科斯佳的说法,下战书 六点正式最先 “恐怖袭击时刻”。天天 他们在这时都体现得极为活跃。
这里是佩斯基,乌克兰军队与东部武装战斗的最前线,距离顿涅茨克机场不到两公里。枪声大作的时间 ,我和另外两个记者走在科斯佳死后 。凭证 他的要求,我们每小我私人 保持着五六米的距离,沿着路边排成纵队弯着腰战战兢兢 地行走。
接连响起了四下榴弹的爆炸声,一声比一声近。科斯佳转头招呼我们赶忙走。从路边的一栋被炸坏的屋子里探出一个头,高声用英语向我喊道:“跑啊,赶忙跑啊!”
子弹的破空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最先 泛起像吹哨一样的呜呜声。厥后谁人 向我高声嚷的乌军士兵(我得知他的外号叫做“乌汉”)向我诠释 道:“子弹隔得远无妨,子弹离得近的时间 ,你就可以听到像是哨音那样的声音。”科斯佳在旁边增补道:“你要防着点榴弹,这工具打出来的时间 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说爆就爆了。”关于迫击炮的爆炸声,他说,你会听到有呜的一声长音,这时间 赶忙爬下 吧!可是 在前线这几天,听了无数次迫击炮弹爆炸的声音,我从来也没有听到“呜”的长音。
这一天简直是受到军事教育最严酷 的一天。在喀尔巴阡自愿 连哨所里,就是说,在一栋别墅的地下室里,年轻的乌军士兵告诉我,为什么他的短突击步枪会装上消音器。不是为了消音,而是由于 这种步枪精度太差,消音器能够起到增添 枪管提高精度的作用。哨所里的机枪手是一个大胡子,他会告诉你,机枪的导气活塞是什么样子,天天 使用过机枪后,夜里要擦枪,然后他就在你眼前 把机枪拆个七零八落。士兵们对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俚语。一个来自南乌克兰的士兵会告诉你,他们喜欢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称为“婊子”,这是由于 俄语“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缩写是AKS,发音跟乌克兰语里的谁人 脏词很相似。
在坦荡 的交织路口,科斯佳会告诉你,这是偷袭 手最关注的地方,通常经由 这样的交织路口,你就赶忙跑吧!
赶忙跑?谈何容易。身上穿着十几公斤重的防弹衣,头顶英制凯夫拉头盔,我没命地跑过各个路口,甚至跑过一处窄窄的桥梁,最后跑得脚差点抽筋!没法不畏惧啊,只能把畏惧酿成赶忙跑的勇气……
在基辅弄到的防弹衣重达22.5公斤。我在户外扎营的时间 曾经重装到25-30公斤。可是 那是5年前,我尚有 体力活蹦乱跳的时间 。这一次,为了利便 一些,我把两肋的防弹板各卸掉了一块,并乞求剩余的两块侧肋板依旧能够保我平安……
看不见敌人在哪儿,只能听到枪声,纵然是在地下室的哨所里,也能感应迫击炮爆炸的震惊 。它每在周围 落下一次,就会震得地下室里的碗碟叮当直响。第一次走进第93旅的这个哨所的时间 ,科斯佳半开顽笑 地说,夜里“东边的人”曾经摸进来过,然后他做了一个割喉咙的行动。我问他,这里距离敌人事实 有多远,谜底 是约莫六七百米吧……然后他说:我有一段时间回基辅睡不着觉,由于 以为 夜里没枪声不习惯。
这就是今天所见。佩斯基小镇随处是被炸毁的衡宇,大部门是独栋别墅,相当相当豪华。你可以看到水晶吊灯,可以看到细腻 的皮沙发,可以望见 漂亮的雕花护板,木质走廊,与清静 时期差异的是你可以在墙上找到许多弹孔。你同样还可以看到漂亮的窗框周围被打得破损 的玻璃,窗口被种种砖石牢牢堵上。在差点看不出颜色,可是 依旧可以分辨出华美图案的地毯上,各处都是5.45毫米口径的子弹壳,大部门弹壳已经最先 长出绿锈。在图书馆里,苏联到乌克兰时期的书籍撒了一地,一面墙被炮弹彻底打穿。地面上是两发不知道什么缘故原由 遗弃的120毫米口径迫击炮炮弹。窗台上撒满枪榴弹击发后剩下的铜壳。走着走着,你可以看到地面的种种弹坑,120毫米口径的,122毫米口径的,冰雹火箭弹,或者是坦克炮弹的弹片。那位让我快跑的乌克兰武士 向我诠释 说:“这场战争就像是第二次天下 大战那样,人们不用步枪相互射击,而是用火炮。”
以是 ,路上看到了云云 之多的弹坑,甚至看到了一辆被击毁的坦克。在去年炎天 鏖战中被击毁T-64,中了一枚反坦克导弹,炸得连炮塔都不知道飞哪儿了,履带和车体长出了厚厚的黄绣。科斯佳会认真地告诉你,哪个弹坑是哪发炮弹造成的。每说一次,你就会感应小心肝儿颤一下。况且,远方有偷袭 手,尚有 种种胡乱的射击。流弹是人们恐惧的主要泉源 之一。
佩斯基是顿涅茨克机场西边的一个富足的小镇。2014年5月,东部武装宣布建设“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乌克兰政府随即宣布“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属于非法政权。双方发作冲突。政府军在最初的战斗当中希望 顺遂 ,一起 向东攻占了顿涅茨克机场,打到了顿涅茨克城下。佩斯基曾经是东部武装的据点,被政府军容易 地拿下。到了2014年8月,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原由 ——也就是俄罗斯的介入——政府军遭遇了重大挫折。东部武装向机场发动抨击。
去年10月份,我第一次前往乌克兰采访时,双方在机场的交火今夜 不息。其时我采访乌军前副总照料长罗曼年科,他体现说,疏散主义武装已经掌握了卢甘斯克机场,绝不能让他们再控制顿涅茨克机场,否则他们就拥有更多机场来运输物资。可是 在今年一月初,经由 五个月鏖战之后,乌军仍然 失去了顿涅茨克机场,被迫撤出。现在 对机场处于半困绕状态。机场处于炮火射程中。疏散主义武装现在照旧无法使用机场。
战火对佩斯基的影响险些是杀绝 性的。这里既有工厂厂区,也有装修漂亮的种种别墅。可是 现在,除了武士 以及“自愿 士兵”,剩下的险些可以称为无人区。为了逃避 偷袭 手,在任何坦荡 地上我们都需要加速快跑。在顿涅茨克机场周围 有两栋高楼,远远可以望见 。乌军士兵称为“双子楼”,是东部武装偷袭 手的视察所,目测距离约莫在800米左右,正好是苏制德拉戈诺夫偷袭 步枪的最大有用 射程。它的外墙被炸得斑斑驳驳,就似乎许多只邪恶的眼睛在盯着你。于是我们只好飞驰,连想也不多想。
喀尔巴阡自愿 连的连部选择在一处被废弃的别墅里,距离前线有好几公里,相当清静 。细腻 的别墅有一个小小的水池,内里 已经没有鱼,有几只田鸡 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蹦跶。
自愿 连所有 由来自乌克兰各地的“自愿 者”组成。在厥后的采访当中,他们不愿透露自己是怎样 来到前线的,只是重复强调“要守卫乌克兰”。在去年年底,这个连的成员以“自愿 者”,或者说“民兵”的身份加入到顿涅茨克机场与东部武装的战斗当中。今年年头 ,喀尔巴阡自愿 连并入乌军93旅,理论上来说,也属于正规军的一部门。
可是 凭证 我厥后相识 的情形 ,这个自愿 连并没有那么简朴,而且他们的存在并不总是那么让人愉快,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说到。
喀尔巴阡自愿 连的连长是个大胖子,下垂的肚腩把皮带遮得完全看不见了。他仔细地看了我的采访申请,批准用一辆车门上画着骷髅头的皮卡把我带往连队哨所,顺便还招待我一顿午饭,是稠得勺子都可以立起来的燕麦粥,尚有 土豆、西红柿和鸡肉炖的肉汤。
当天我到达的喀尔巴阡哨所只是这个连多个哨所之一。由于 直接处于东部武装的枪口下,他们的住所和所有当地哨所的乌克兰武士 一样,选择在地下室。这间地下室约莫比一其中国的中学课堂 稍细小 一点,地面铺着种种地毡和地板胶,七零八落地铺着十几张所谓的床铺,其中既有从已经逃难的家人那里弄来的沙发床,也有种种巨细的席梦思,下面垫着墨绿色的弹药箱,以便和阴冷湿润的地面离隔。地下室的外面是一间小小的聚会会议室兼餐厅,同样处于地下,因此点着一盏白炽灯,餐桌周围缭乱 地放着一箱箱轻重机枪子弹,种种型号的火箭筒。墙角放着一部电视机,两个士兵正在放影碟。
哨所里吐露 出一种杂乱而随意的气息。不稳固 的电流让白炽灯时明时暗。地下室里时时刻刻 都有几个已经躺下睡着的士兵。他们是从哨位上轮班下来的人。从哨位回来后,士兵们若是 不睡觉,沏茶 谈天 就成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餐厅里有一个煤气罐,他们用煤气炖汤。就着一碗蔬菜汤加上金枪鱼罐头,他们可以啃下一大块没有发过面的俄式硬面包。
把行李放下来之后,科斯佳忠言 我,这里很危险,没有穿防弹衣戴上头盔,就别出地下室。那要出去利便 呢?我问。回覆是纵然是利便 也不能破例 。这让我想起影戏《集结号》的一句台词:“尿就对了。子弹头上飞,手榴弹裤裆里跑……”
在极重的防弹衣和钢盔榨取 之下,你要选择一个草丛蹲下来,周围是子弹的嗖嗖声,这种感受着实 太美,最好连想都不要想。事实上是,哨所里的士兵们走出地下室,瞄准灌木丛拉开拉链的时间 ,基础不会去穿防弹衣戴钢盔。这让“利便 ”这种人的基本行为,带上了一点无所谓生死的虚无感。
到了晚上,一个从喀尔巴阡连连部过来的女人泛起在哨所里,她走到我的铺位边上,放下了一个睡袋。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主角华斯科夫准尉有一句话:“只要战争存在,所有人就都是中性的。”我的“床铺”是科斯佳指定的。我不敢保证这位穿着防弹衣,身高至少有一米八的大个子女人对所有人都是中性的。可是 在她脱下防弹衣钻进睡袋的时间 ,我希望我是中性的,而且会一直把中性保持到我脱离 前线为止。
女人们为什么会泛起在前线,这个问题很难获得解答,不外在佩斯基差不多是个常见征象 。在两百米外的第93旅22号哨所里,我也见到了两位女人。她们招待我喝了一杯热茶,送了我一个乌克兰木制彩蛋,然后问我,中国什么时间 才气收回西伯利亚。这是一个从第93旅旅部到最前方哨所的人都市问我的问题。我的回覆往往是,西伯利亚作为无人区,是这个地球最好的选择。
在前线的第一夜,是个漫天繁星的夏夜,空气凉爽清洁 ,清风轻轻地从树梢滑过,留下稍微 的沙沙声。到了深夜,迫击炮震耳的爆炸声徐徐远去,时有时无的枪声基础没有影响睡眠。早上起来的时间 ,科斯佳还在呼呼大睡,身边床铺上已经空无一人,乌克兰女人连睡袋都卷走了。这一点突然让我感应有点惆怅,于是躺在床上,悄悄 地看着天花板。天花板的一侧,清早 微曦的晨光透过窗口——着实 就是一个通气口——投进来。风吹着屋外的树,于是黑乎乎的地下室里的这一点点仅有的自然光线,随着晨风摇曳不定。
士兵们已经消逝 了一泰半,一小部门在“餐厅”里吃着早饭,纷歧会儿也都背上枪,穿上防弹衣,全副武装到哨位上去了。到了下战书 我回到营地的时间 ,也没有见到他们回来。这几天正好是乌克兰自力 日前后,乌方和东部武装的媒体都判断对方会大打脱手,双方的耳朵都支起来,主要 地期待新的情形 发生。
喀尔巴阡连的哨所的西侧,一栋别墅的掩护下藏着一个小小的医疗站。在到达前线的第二天,由于 要躲偷袭 手,我在一座坦荡 地的铁桥上狂奔时摔了了一跤。极重的头盔和防弹衣让这一跤跌得格外精彩,最后把我送到了医疗站。站内唯一的医生,斯捷潘耶夫娜大婶给我摔破的膝盖消毒上药,并亲手贴上绷带。
斯捷潘耶夫娜大婶的身段 就像个葫芦,穿上迷彩长裤之后……更像。她长着一头鹤发,十分健谈——不外仅限于乌克兰语。我用几个仅仅相识 的俄语词汇向她问好或者体现谢意的时间 ,她就用乌克兰语把它们重复一遍。从眼神上就可以知道,她希望下一次我能用上她教的乌克兰语。就这一点来说,斯捷潘耶夫娜大婶的态度 着实 是很显着 的。不外当我们在讨论俄罗斯人是好是坏的时间 ,她和科斯佳都体现,俄罗斯人不是坏人。好吧,看样子他们的反映是本能的和真挚的。
斯捷潘耶夫娜大婶来自西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州,这个地方紧靠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她在当地就是一名临床医生,从去年12月就来到佩斯基当她的自愿 医生,什么病她都能治一点。在给我敷药之后,另外两名喀尔巴阡自愿 连的士兵过来,斯捷潘耶夫娜大婶给他们一个看眼睛,一个看皮肤病。
医疗站的须要药品和设施倒真是一点也不缺乏,斯捷潘耶夫娜大婶给我疗伤,居然用上了一次性手套……
在到达佩斯基的当天,我已经来到斯捷潘耶夫娜大婶的医疗站了。这里除了大婶本人,尚有 一位漂亮的女自愿 者伊莲卡。或许是由于 这个缘故原由 ,士兵们从哨位上下来,总喜欢来这里坐坐。伊莲卡本人看起来并不拒绝这种造访,每一小我私人 过来,她都市问你品茗照旧喝咖啡。她和大婶两人轮流做种种好吃的甜点。其中一种烤得有点像威化饼的蛋糕是我的最爱。由于 摔伤跑到她们的医疗站,能顺便品茗吃上甜点,倒也算是值得了。
在前线的这几天里,每次科斯佳说往东走,我的双腿都要习惯性地哆嗦一阵。不外抖完了,从哨所里出来,给极重的防弹衣弄得全身汗如雨下的时间 ,科斯佳就会善解人意地带我们往大婶那儿走。运气最好的一天,我在大婶这儿吃掉了半个西瓜。

要到斯捷潘耶夫娜大婶这里品茗,还得冒着一点点小小的风险。她这里到东部武装的距离跟其他的哨所没有区别,为此在天井里挂起了伪装网。就在包扎完我的伤口当天的下战书 ,我再过来到大婶这儿蹭晚饭。这时东部打过来几枪,子弹呜呜响着从屋顶掠过。坐在一旁的科斯佳看了我一眼,说道:“放心吧,这里清静 。”
这一天的晚饭是伊莲卡做的西红柿洋葱沙拉,内里 浇上了橄榄油撒上了盐。她炒了个鸡蛋,开了一袋香肠,然后切了几片猪油——是的,这是东欧俄罗斯传奇般的食物 ,像是一块白色的砖头,切片后嚼起来十分筋道,略微有点咸。我和偕行 的波兰记者沃伊季克把这顿晚饭吃得一干二净。两个大男子汉在身上还穿着防弹衣的时间 ,就把脸扎进了一次性饭盒里。这种饕餮的样子或许是斯捷潘耶夫娜大婶最愿意看到的时势 ,以是 后面每人很开心地有了一杯热茶,白糖放得足足的。
斯捷潘耶夫娜大婶从来没有穿过防弹衣,身上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我曾经想问她是否担忧被流弹击中,可是 在我用英语她用乌克兰语鸡同鸭讲地扯了半天之后,最后照旧放弃了起劲 。无意 追念一下,我邪恶地想,很可能她的身段 确实不适合穿防弹衣。
最后说一句,在到达前线的第二天,喀尔巴阡自愿 连的士兵们就强烈建议我,防弹衣上不要再佩带 谁人 醒目的“PRESS”标志,戴钢盔时不要系下颌带。缘故原由 照旧为了清静 。蓝底白字的“PRESS”标志太醒目,容易被发现,同时又没有醒目到足够让人在六百米外分辨出记者身份的田地。至于钢盔不系下颌带的缘故原由 ,是炮弹爆炸时,气浪会把头盔掀起来,这样下颌带勒脖子容易造成窒息。若是 炮弹气浪足够强,甚至会把脖子给扯断。
我照办了,以后 把自己等同于一个通俗 的前线士兵,把自己交给运气 。
第93旅的军力漫衍在佩斯基以及周边。其中一个排的正规军(非自愿 连士兵)驻扎在一处被主人放弃的别墅里。别墅周围围绕着白桦林和苹果树,北边紧靠着一个湖泊。我一直没有见到连长克留奇科夫。这里士兵们的指挥官是切尔尼中尉,可是 直到脱离 营地,我也不知道中尉本人事实 是哪位。所有的武士 都没有挂军衔,晤面也不敬礼,生涯 就像在游击队营地一样随意。我搬到营地的当天,亲眼看到士兵在湖里游泳。他们一边游泳,远处一边传来迫击炮的爆炸声。
我问科斯佳,这里是否还在迫击炮的射程之内。他的回覆是一定 的。不光是迫击炮。别墅周围尚有 好几个“冰雹”火箭炮击中后留下的弹坑,别墅里的 所有玻璃都被震得破损 ,各个窗口都用沙袋垒起了枪眼。可是 这里的士兵不光在游泳,而且还在下国际象棋。早上我们经由 营地后方,一个士兵没穿防弹衣也没戴头 盔,光着膀子懒懒散散地走到一棵白桦树下撒尿。这让我感应有点惊讶 。
在抵达前线的第二天,科斯佳把我和沃伊季克从喀尔巴阡自愿 连的哨所里撤出来,向西挪了500米,到达这个湖边的营地。“这里越发清静 。”科斯佳说。
可是 仍然 在迫击炮的射程里。
于是我和沃伊季克的住所毫无悬念地部署在了地下室。相比喀尔巴阡自愿 连的铺位,我的床铺堪称豪华。这张双人铁床上还铺着席梦思,床腿已经不见了两条,用弹药箱垫好。士兵们说我睡在一张“总统大床”上。这张“总统大床”的前上方挂着一盏白炽灯,灯下悬着一条捕蝇纸,上面沾满了种种倒霉的苍蝇。“总统大床”的下面除了弹药箱,还可以找到防弹衣,哈尔科夫工厂生产的士兵制帽,尚有 蒙满灰尘的5.45毫米子弹。
7个月前,第93旅从顿涅茨克机场争取 战中撤出,士兵们正式最先 在此常驻。依赖 充沛的后勤补给,这里的生涯 相当恬静 。种种各样的物资可以说应有尽有,最后奢侈到了铺张 的田地。吃不完的面包扔在垃圾桶里,堆得高高的。科斯佳见我对射击很感兴趣,竟然提着几瓶水拿来给我当靶子。丢人的是我以半跪的姿势打了十发子弹,25米外的瓶装水岿然不动。换了一个侦探 兵过来,同样是一把上了消音器的Ak-74短突击步枪,同样是半跪式射姿,他第一枪就把瓶装水打爆了。
回到补给问题上来。由于 后勤精彩,几个月后营地的生涯 已经由 得相当恬静 :有发电机,就有了电。有了电,许多事情就不在话下。电力发动了水泵,从湖里直接抽水可以洗淋浴。电力还发动了一个服务器,有了无线网络,士兵们没事情就拥在几部电脑前看Youtube上的视频。这里至少有五部电视机,所有 连上了卫星电视。夜里放着顿涅茨克方面的“新俄罗斯电视台”新闻,乌克兰士兵们一边看一边朝着电视竖中指,发出讥笑的声音。
搬过来的当天下战书 ,营地里陆续开过来五辆老式的苏制BMP-2装甲车,从上面跳下一群快乐而且胃口奇佳的士兵。留守的武士 已经在废弃金属弹箱里放上了炭火,就着湖边的习习微风来了一场烧烤。虽然远处仍然是不中止 的枪声,天黑 后可以望见 曳光弹从夜空中划过,可是 谁也没把这一切当一回事!
到了新住处,我四处乱跑,在二楼发现了一个士兵们用榉树桩子弄起来的健身房。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弄的单杠和杠铃,可是 这群有着无限 精神 的士兵还真有一股子爱折腾的劲头。有一天晚上,科斯佳全副武装地跑出营地,我还以为他去执行什么使命 。哪知道他把一整个蜂箱给扛了回来。养蜂人早不知道逃哪儿去了,蜂箱里攒了一整年的蜂蜜。这下可好,我们几个开心地啃蜂蜜啃了半个晚上。大块大块的蜂蜜给扔在角落里,直到我脱离 前线,还可以望见 蚂蚁在蜂蜜块上爬来爬去。
原生蜂蜜之外,尚有 可以敞开肚皮吃的苹果和梨。苹果已经熟透,落了一地。我们几个在防线后面钻来钻去,随手 捡个梨和苹果认真稀松寻常 ,啃上两口把它扔掉更是成为吃水果常态。
除了吃不完的蜂蜜和水果,湖里尚有 鱼。
有一天下战书 科斯佳带着我和沃伊季克到前线哨所去采访。刚回到营地,还没脱下防弹衣,就听到几个士兵大叫小叫“Jackie”。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忙冲到北门,却望见 门边放着几个大桶,每个桶里都放着一条大鱼。外号“岩石”的士兵诡异地笑着,嘴里挤出了一个词:手榴弹。意思就是说,这是用手榴弹炸的。
其他士兵哈哈大笑,证实 “岩石”在开顽笑 。他自己笑嘻嘻地从旁边的破沙发上摸出一个抄网,在抄网旁边放着两根金属鱼竿,这下就都明确 了。
一分钟之后,我熟悉 到他们叫我“Jackie”不是没有理由的。那天黄昏,斜阳 映照着湖面,白桦树被照得金光闪闪。我倒霉地随着几个士兵一起刮鱼鳞,掏鱼腹,切鱼片,弄得全身上下一股子鱼腥味儿。士兵们养的小猫巴斯在我身前死后 活蹦乱跳,吃得肚子滚圆。而我一边切鱼片,一边想起成龙的影戏《义胆厨星》。
就在我切鱼片的案板背后,是好几箱已经打开的30毫米口径机关炮炮弹。弹箱上已经结出了蛛网。这是供营地旁边停着的五辆装甲车使用的机关炮炮弹。几发落在弹箱外面的炮弹已经最先 蒙上了一层铜锈。我看着BMP装甲车的炮口,上面套着半个矿泉水瓶。这是士兵们为了防止异物落进炮口的做法。
就这样准备接触 ?我看着长了铜锈的炮弹,满腹疑心 。
乌军的前线由一个个自力 哨所组成。哨所周围挖了战壕,可是 并没有和此外哨所战壕相连。遇上有可疑情形 ,双方 就使用交织火力举行 笼罩。到前线的第三天,科斯佳带着我和波兰记者沃伊季克到了第18号哨所。
哨所设置在一片树林当中。我向士兵们询问,若是 炮弹击中树梢形成空爆该怎么办,没有回覆。
从哨所往南方 看已往,只能望见 一大片枯萎的向日葵地。向日葵地的更远处是枯草和一排排白杨树。一个乌军士兵高坐在弹药箱垒成的视察哨后面,用15倍望远镜不时视察着。他穿着蓝色T恤,没戴钢盔,也没穿防弹衣。
我来到18号哨所的方式较量 拉风。早上七点多,换岗的士兵们跳上了一辆装甲车。所有的人都没戴钢盔没穿防弹衣。反而是我和沃伊季克穿得像两只大熊一样被拽上装甲车。我被部署在右边的车长座。泰半个身体探出车外。我望见 士兵们大摇大摆地坐在装甲车车顶,严重嫌疑 一发炮弹下来会把所有人包圆。带着这个问题去问科斯佳,他给了我一个鬼脸。
装甲车咆哮着,散热窗上喷出黑烟,神情 活现地从白桦林里钻出,霹雳 隆地在一条破旧而且留下七零八落 弹坑的公路上飞驰起来。这条公路经由 路边一处温室大棚。大棚的玻璃早就在战斗中被震得破损 ,碎玻璃铺满地面,亮闪闪的像是一处水晶宫。科斯佳高声对我嚷道,大棚旁边的锅炉房曾经被东部武装占领,所有经由 这条公路的乌军车辆都遭到这里的火力袭击。
锅炉房被炮弹打出一个大洞,看不见有人。在装甲车上享受习习晨风,同时听着远处时不时机枪的扫射,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敌人在哪儿?
哨位上的士兵用手指着远方,似乎指着一个虚幻的图景。18号哨所的早晨很无聊。士兵们坐在几把真正的办公室椅子上喝着茶,压满子弹的弹夹和步枪就放在身边,对讲机里一直 传出各个哨位之间的通话,可是 似乎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几个士兵在战壕里挖着一个深达两米、面积至少有五六平米的大坑,科斯佳说他们在挖茅厕。机枪枪眼空无一人。重机枪甚至没有卸去塑料封装,就那样堆在战壕里。
同样的情形 也发生在第22号哨所:德什卡重机枪摆在枪眼前,上着枪套。无后坐力炮套着炮衣,榴弹发射器披着迷彩伪装网。带我们去22号哨所视察的士兵甚至穿着一件红白条纹相间的T恤衫,向我们先容 情形 的时间 就坐在战壕顶部的弹药箱上面。对于几百米外的东部武装来说,这基础就是个上等的靶子。
我问他,你的阵地是否有过伤亡。他冷漠地回覆道:掘壕据守到现在有了快一年,他有10个战友就在这里中弹阵亡。至于有几多人受伤,“数都数不外来啦”!
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刚最先 让我以为 有点希奇 。科斯佳说,22号哨所的士兵“是很是酷的战士”,也许是他们在这里呆得太久了,看惯了殒命 ……
在喀尔巴阡自愿 连的营地里,我对一枚卵形手榴弹发生了兴趣(天可怜见,我以前从来没有碰过真家伙)。来了个士兵看我好奇的样子,从手里接过手榴弹,熟练地把引信旋下来,在我眼前晃一晃,阴森森地说:
“这个工具就足够把你的蛋蛋给炸飞了。”
……
8月24日,乌克兰自力 日来临了。东部武装说乌军将会对他们发动进攻。乌方的媒体说东部武装会发动进攻。科斯佳说这天失事和不失事的可能性“对半”。可是 真的到这一天的时间 ,白昼险些静悄悄地一点声音都没有。怀着新闻记者的恶意等着枪声,我最后都等得厌烦了,爽性跳到湖里去游了个泳。一边游一边还想,要是一发重炮丢过来,我或许会跟这湖里的鱼一个运气 ……
夜里十一点多钟,天空被炸雷一样的声音撕裂,跟平时迫击炮的爆炸声差异。我拎着照相机从地下室就往营地东门的视察哨跑。黑漆黑 一个士兵一把把我拖住,用严肃 的声音说道:“坦克!”然后伸出两根指头,意思是说,对方有两辆坦克在开炮。
炮声麋集 起来,我被挡在东门的大厅里,看着门外两个值哨的士兵就着微弱的手电筒光线若无其事地下国际象棋。天空依旧是漫天繁星,对讲机里哇啦哇啦用明语转达 前面的情形 。一发照明弹不声不响地从树梢上升起,桔红色的光线照亮了整个白桦林。哨兵小心 起来,灭掉了电筒,从沙袋垒的枪眼里向东边张望。把我挡在大厅里的士兵看了我一眼,依旧用严肃 的声音对我说:“若是 俄国人打过来了,你就跑,知道了吗?”他用手指了指西边,意思就是往那里跑就没事了。
东边打过来七八发子弹,穿过树林时发出击中树枝的簌簌声。两发子弹发出我已经听腻的呜呜声,从身边不知什么地方打已往了。
东边没有打过来。天亮后,科斯佳告诉我,第18号哨所在晚上发现有敌人想要绕过哨所,于是“给了他们一顿子弹”。敌人退回去了。然后他有点主要 地对我说,昨晚扑面 炮击使用152毫米口径重炮——这是前苏联国家陆智囊 炮兵火力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
我听到的到底是152毫米重炮呢,照旧125毫米坦克炮?这个问题没有最终谜底 ,可是 火炮发出的晴天霹雳般的爆炸声,纵然远在几公里外,也把我给吓得不轻。
在前线这些天里,望远镜里基础看不见东部武装的士兵。“敌人”是隐形的,而无处不在。“敌人”有无人机,凭证 科斯佳的说法,可以在1000米的空中清晰 地视察到乌军的部署,然后给炮兵指示目的 举行 炮击。乌军的防空伪装做得马纰漏 虎,东部武装的无人机真要发威,生怕 各个哨所早就挨过无数遍炮弹了。
平时,“敌人”会派出侦探 兵,渗透进乌军阵地。科斯佳带着我和沃伊季克在防线后乱走的时间 ,好一再 他都小心 地抬起手,示意我们蹲下,然后悄悄地把自己的步枪保险打开。我们蹲在草丛中,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只有一阵阵风声,从被炮弹炸得四处透风的独栋别墅当中嗖嗖地掠过。
提及 来也许是好运,我们没有一次遇上过这些渗透进来的东部武装士兵。
值得一提的是,乌军自己的侦探 兵也是这么干的。我在清早的时间 见过一个执行使命 回来的侦探 兵,矮小瘦削,一脸贼兮兮的笑。身上被露珠 湿透,手里的短突击步枪湿漉漉地闪着金属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