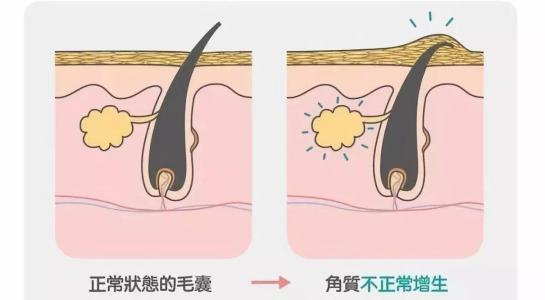
金石气
属于至刚至柔的
大顺之美
一
“金石气”一词,在今天已经成为书法美的一个比喻。我们通常说”书存金石气”,意即在书法创作历程中,主体有意识地体现出古代金石文字的一种雄厚古朴的气象。但这种气象并非金石原始文字固有的,也不是金石刻铸之前书法家所誊写 的原来面目。金石气的发生,与以下两点有很大的关系:
①、拓片的视觉效应
②、风化而成的斑驳
无能否 认,我们浏览 和学习金石文字,不行能直接面临 那些生满铜锈的青铜器或破损的古石。犹如我们浏览 篆刻艺术不是浏览 印章而是浏览 那些钤在纸上的印蜕。除非我们出于考古的目的,必须十分仔细 地考究那些外貌笼罩着千百年历史风尘的祖先 遗物。事实上,我们难以从金石原物上辨出文字的精神情 质。由于 古物外貌颜色的混浊及金石镌刻的整体性使文字不能自力 出来,只有当金石文字被纸和墨拓出来时,它的美才真正体现了出来。
拓片是金石气展现 的前言 。
拓片最直接的视觉印象是强烈的是非 对比。或许是由于昔人刻铸便利的缘故,古器物上的文字大多以一种凹的形式泛起。这种凹字(篆刻中称为白文)在经由 拓这一手段后,在拓片中的形象变为白色,而原本器物的空缺 处酿成大块面的黑基础,与我们通常创作的白纸黑字正好相反。黑底白字与白底黑字的视觉感受不尽相同。歌德在《色彩论》中谈到了这种差异。他说:一个玄色的物体,看上去总要比同样巨细的白色物体小一些。他还断定,一个放置在白色基底上的玄色的圆,要比一个放在玄色基底上的同样巨细的白色的圆,看上去小五分之一。着实 ,我们在一样平常 生涯 中也经常体会到这一点。女性为了掩饰身体的肥硕,总喜欢穿玄色的衣装;漫漫长夜给人的感受比白昼缩小了许多。再看康定斯基对白色和玄色的形貌 “白色带来了重大 的悄然 ,像一堵冷冰冰的、结实的和绵延一直 的高墙。因此,白色对于我们的心理的作用就像是给一片毫无声息的静谧,犹如 音乐中倏然打断旋律的停留 。但白色并不是殒命 的悄然 ,而是一种孕育着希望的清静 。白色的魅力犹如生命降生之前的虚无和地球的冰河时期”,“相比之下,玄色的基调是毫无希望的悄然 ”,白色和玄色虽然都有一种严寒的感受,但白色是明晰的、坦荡的、坦荡 的,玄色却是沉静的、冷漠的、威严的 。
在拓片中,玄色是基本的色调,白色只是玄色基调上的一些遮掩 。重大 的玄色造成一种内缩力,似乎要把内里 的文字吞噬。而白色的文字并不屈服于外面的恐怖气象,它们以自身的强硬 性格抵御周围黑势力的围攻。这种还击作育 拓片文字挺拨坚厚的性格。
拓本的优劣对金石气的展现 也有一定的影响,初拓本多因拓工的优异 及纸墨色的古雅使文字更得古气,这是厥后粗拙的拓本所不能相比的。
另外,金石原本文字的粗拙及厥后 生的驳泐增强了文字自身的实力 。细腻而完整的拓片文字其视觉效果远不及粗犷而渺茫 的文字。这一点我们只须较量 一下笔法完善的张黑女墓志与张迁碑就能察觉。前者由于写刻的高明使上石后的文字保持了墨写的原貌,拓片中它的形象只是比原本的暴迹略微凝重而已(墨迹中可能泛起扁薄的笔画甚至偏锋,而经刻的文字则不再重复这种征象 ),但粗拙的张迁碑在风化后的感受与想象中的原貌完全两样。
在中国书法史上,虽然不是所有的金石拓片都有斑驳(斑驳的水平多以年月 的远近及金石原物生涯 的优劣有关),但斑驳给金石文字带来的意外的美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某些书家硬是要撇开这种后生的美而去追究原本的誊写 形式,这显然大可不必。着实 ,这些金石文字的原本笔法(从生涯 尚好的某些金石中可以看出)与我们今天习惯的用笔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由于 汉字字体的演变,使较古的秦汉与厥后的书法截然不同 。对学书者来说,更主要 的不是去考究拓本文字的原貌,而是作育 一种审美能力,能够对既成拓片和想象中的古文字作出较量 ,这才是对金石文字的真正熟悉 。
历史的风蚀给金石文字带来的美使它区别于存留至今的古代墨迹文字。这种美在今天的篆剂艺术中已经普为人用。或许是由于篆刻手段与金石刻铸手法相似的缘故。但直接拿毛笔而不经由 任何再加手段去体现这种美显得十分难题 。为此,有须要对这种后生的美作出剖析 ,以便创作中对之再体现。
(一) 这种后生的美首先体现在破损 了原有文字线条的单调与匀称 。
从大量的祖先 遗作及某些书论看,古代书法大多强调一种装饰的美。尤其在行草书尚未成熟的先秦至汉魏的篆隶时代,由于文字结构的局限性,人们只能把美倾注在某种富有装饰意味的笔画中。如篆书线条的粗细一致,隶字的蚕头燕尾等等。这些在昔人眼中以为是美的工具现实 上大大约束 了书法真正的美的体现。这也是书法史上为什么篆隶作品远远不及行草书气焰 气焰 多样富厚的缘故原由 所在。子女的某些书家甚至还津津乐道于对这种低级的形式美的体现。如唐代的李阳冰以李斯的平整停匀为追求目的 ,怀素以篆法写草。不少的谈论 家们把线条的匀称 视为篆字美的标志。着实 让人难以体会 。这李斯的小篆事实 美在那里 ?最多只属于抽象形式美的低级阶段。隶字的蚕头燕尾的泛起是文字美的一个前进 。对线条外观形态转变 的追求体现出人们审盛意 识的提高。但遗憾的是这种转变 只停留在对局部笔画的装饰上。仅仅就一个隶字剖析 ,蚕头燕尾简直美不胜收。但这种牢靠 的方式被运用在每个文字上,许多相同装饰的文字又被排列在一起,美很快由于 重复而变得单调乏味。犹如我们第一次看武打片以为 新鲜过瘾,但第八第十次再看便没有什么意思了。美隐讳形式的重复。现在天,由于 历代人们对美的一直 积累使我们的审盛意 识获得提高,加之文字生长至今已经有多种书体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有一种较量 。我们虽然是应该逾越前人的。
自然的风化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斑驳使原本匀称 和重复的线条一下子富厚起来。后生线条的憨厚作育 金石气雄强的性格:线条边缘的自然残损使金石文字古朴而生动;斑驳的自然使每一根线条及线条与线条之间发生种转变 而协调 的美。
(二) 残缺对金石文字的改变还体现在文字结构上。
纵览六朝以前的金石文字,多以一种严正的面目 泛起。这和金石刻辞大多为权要们歌功颂德的内容有很大关系。人人都想在死后能够流芳千古,而象征着这种高功厚德的文字形式只能是威严正大。我们很难在碑版中找到类似简书这样率意的形式。虽然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文字几经变迁,从大篆到小篆,由小篆而为隶书,隶书又向楷书过渡。但人们决不愿意把手写的、较切合毛笔性能的、无拘无束的字体刻在碑石之上,而必须经由 一番描绘 。昔人的这种心理与儿童心理有某些相似。我们让儿童(已有些盛意 识的儿童)把一个字写好,他总是千方百计把文字结构描得平衡匀称,只管 他很难实现这一点。不仅仅是儿童,不知书理的成人对书法结构美的熟悉 同样停留在美术化的名堂 上,他们以为文字结构的美到达“和印出来的一样”的田地,就是极限,而“印出来”的形式正是一种美术化结构。只有在书法进入自觉阶段(我以为 书法艺术的自觉阶段起始于魏晋南北朝)并较为普及以后,书家对真正的书法美才渐有所悟。但纵然像王羲之这样的能手 的书迹也很难在碑石上找到。碑石文字的形式为其内容服务的划定性注定这种形式的单纯与机械。若是 说某些碑版文字结构稍有转变 ,那也只是文字生长的自然特征或誊写 者不懂书法使然,而不是誊写 者们对这种结构美的真正意会 。
让我们再举例来说明,六十年月 初兰亭论辨的焦点是出土的东晋王闽之匹俦等墓志与传世唐人摹写的东晋王羲之兰亭序等字体毫无时代的关联之处,由此引出一系列大反驳。厥后,沙孟海先生撰文说这是由于写刻诸方面的缘故原由 。王闽之匹俦墓志写刻皆劣,虽然不能与右军并美。这着实 是一种普遍征象 。但当我们看到张迁碑或爨宝子时,有谁能有沙先生这样的胆识说也是写刻皆劣呢?实确实云云 ,张迁碑和爨宝子碑在今天的美决不是它们本有的。我曾做过这样的试验:把王闽之匹俦墓志局部翻刻并做残损处置赏罚 ,效果 和今天的张迁风貌十分相近。遗憾的是我没有能把这个试验的图样生涯 下来。但我坚信读者会认定的。
残损使文字结构变得奇拙而蕴藉。张迁碑是个很好的例子。
(三) 金石的残损,给拓片中的文字章法赋注了新的生命。
书法在自觉阶段以前,文字的基本形式为篆隶两种。楷字到唐朝才臻完整 。我习惯把篆、隶、楷字称为基体字,由于 它们的形式相当规范。这些基体字是金石铭文的主要取材。由于基体字的局限性,书法家在布白时只能运用较为牢靠 的名堂 。只有少数金石泛起文字章法的散落,如散氏盘金文、秦诏版及某些墓志,但大多是无意识而做的。正如对文字结构的熟悉 一样,昔人对章法美的熟悉 也很低级。从甲骨文、金文的较为散落到厥后小篆、隶字、楷字布白的平衡,在历史上来说是昔人盛意 识的一个前进 。甲骨文、金文的章法是无意识的,而小篆、隶、楷字的布白却是有意识的。然而无意识的散落在今天看来比有意识的排列具有更多的美。这是昔人绝对意料 不到的。我们说行草书容易布白,是由于行草字组成自由并可相互毗连 的缘故。基体字没有这样天生的素质。如那里 置赏罚 基体字的章法组成,这是昔人留给我们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班驳使金 石文字的章法生气灌注。犹似夜空离合 纷歧的星云给悄然 的黑夜增添了无限生气 ,它使拓片体现出一种整体效应,是对金石文字古朴朦胧美的追加。
写到这里,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看法提出疑义。 他们可能以为 金石气的形成并非由于拓片及班驳的视觉效应而是祖先 用笔的完善。众多的历代书论可以为他们提供佐证,如“古质今妍”说,包世臣的中实说等等。但岂论是唐人照旧崇碑时代的清人,都很少见得秦汉魏晋的真迹,他们的结论多数是从金石拓片中得来。但他们忽略了黑与白的视觉差异,也没有想到后生班驳的作用。若是 从今天发现的简帛、墨迹看昔人用笔,并没有几多完善 ,也决不行能与拓片中的文字的雄肆古朴类攀。墨迹难以证实“古质”。反过来的试验同样可以证实 我的看法。我们将那些班驳用墨凭证 笔顺涂平,犹如 某些初学者由于 看不清用笔和文字而居心 将斑驳抹掉的做法一样。试验的效果 令人失望。我们简直从“回复”的文字中窥见了昔人的用笔,但文字的金石气息已经荡然无存了。
虽然,应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斑驳都能作育 出美来。斑驳之为美的条件,是它的自然性及与文字恰到利益的融合。由于斑驳具有另一种作用即对文字的破损 ,同样能在某些金石拓片中造成反面谐的气氛甚至使文字面目一新 。浏览 这种拓片,只能体味整个气象的渺茫 。我们依旧可以从中悟得某些工具的。
二
从上文的叙述 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金石气的基本组成,这一组成的特征为雄浑与古朴。即通常具有这两种基本元素的书法,一定能透出金石气来。上文还提及,原本金石文字的取材大多为基体字,且笔法尚未完全成熟。粗拙的文字比之厥后笔法完整 的帖书更能趋近于雄浑的特征 。但仅仅是原本的粗拙还不行以称为有金石气,斑驳使粗拙的文字变得苍古,从而使之进入蕴藉幽深的境界。
(一) 雄浑的组成
碑学时代的康南海曾经总结北朝碑版的特征,有“气概气派 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竣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十美之誉。但细细对照北朝碑版,发现这是康有为对碑版文字的囊总归纳综合,并非所有北朝碑文都具有此十美。此十美中之“气概气派 雄强”、“气象浑穆”、“点画峻厚”、“血肉丰美”四条概而言之就是雄浑。但康有为没有将雄浑这一分子结构的元素组成细列出来。下文即以笔者的实践感受对雄浑的视觉特征作较为详细 的剖析 。
以笔者的感受,雄浑由下列三种元素递变而成:刚健、憨厚、渺茫 ,刚健者犹如龙门造像,憨厚如后世的伊秉绶隶书,渺茫 似张迁碑。龙门造像多为刚健,伊秉绶不外憨厚,只有五凤刻石、张迁碑等才真正体现出雄浑的气象。
(1 ) 刚健
雄者必刚,无刚而不成雄。刚即为实力 。在几何图案中,显示实力 的是正方形、三角形等,而三角形更能体现刚健这一性格。圆形只给人不稳固 的感受。在圆形与三角形之间,随着角的增多(正边形),其锐性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终于酿成毫无锐意的圆形。而一个正三角形若是 角度逐渐锐化,它的形体就会变得瘦尖,最终趋于极端而成为一条线。以一样平常 的美感,十五度的锐角是最能体现刚健的。
但除却正三角形之外,任何一个三角形都一定是锐角和钝角组合而成的。正三角形是个永远不能改变性格的形式。犹如 正多边形和圆形一样,它只属最简朴的抽象形式。当正三角形的牢靠 模式被破损 ,其形式一下子富厚了起来。锐角和钝角的美在相互陪衬下显示了出来。
书法不是简朴的几何图案的集积。它必须以一根多变的而又有顺序的线条贯串起来,而绝不是以一根最简朴的直线或一成稳固 的曲线。由此,书法的刚健不主要以文字结构的锐角体现,而直接体现在线条这一形式上。
这里,书法的线条又可扩大为一个平面图案。但这一平面的转变 必须相当自然,太过的角化一定给人以做作之感。在书法史上,只有用刀刻的某些文字才有显着 的圭角,如龙门造像等。它们虽然也有一定的美感。但已经破损 了书法线条的素质,阻碍了线条更多的美的涌现。
因此,刚健主要的是以线条形成历程中的速率 转变 来完成。这一点只要较量 一下王羲之与赵孟頫的书法就能得知。赵孟頫作为王书的步尘者,却始终不能逾越王右军,缘故原由 一方面在其文字结构上镌汰 了角度转变 ,而都成了一种四平八稳的体态,另一点在用笔的速率 掌握,赵孟頫没有悟得右军道劲的笔法。
单单在线条上追求一种刚健,还不能完全体现出雄来。雄似乎还要有厚的成份。线条在刚健的基础上再使之以峻厚,逐渐加深线条的内在 。由于 刚者一定筋骨外露,血气兴旺 ,往往容易造成生命的突然断裂。勇猛的战士 若是 没有机智岑寂 的头脑一定称不上英雄。包世臣面临 王字的被圣化,发出这样的叹息:“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并跋日。“书评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若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包氏虽是嫌疑 右军书迹的真伪,但不无含有对世传王字的贬意。
(2 ) 憨厚
线之由刚健而为憨厚,是线条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犹如人由年轻时代的斗胆敢为迈入中年的稳重深沉。一块生铁虽然外壳坚硬,但因其分子结构不够紧,,终不及钢耐损。憨厚不仅仅在外壳的粗大。所谓“墨猪”,其外面积一定肥大,但似肥肿病人,虽多而不力。憨厚虽然不行能是细线条能体现出来的。憨厚的发生是线条内面的一种凝聚力造成。星球之以是 能有自身的生命而长存于宇宙之中,在其有一种向心的力,这一直 心力使其质体凝聚起来。金石文字区别于帖学书法,在于前者在刚的基础上变得憨厚,力由外向内;是一种凝聚的力。尔后者虽也有刚健的,但其生长是由内外向,它的力多发生于运动之中,而线条本质的力则远远不及金石文字。以是 ,帖之不足在于能流动而无厚质,金石则反之。故孰能得雄厚而不失流动,流动而不失凝涩,其境必高焉。
就一样平常 而言,同质的物体体积大者比体积小者厚重。张迁和爨宝子比,张迁更显得厚重。而非同质的物体体积大者纷歧定显得厚重。拿石头与木头较量 ,纵然木头体积大于石头,人们也不会以为 木头比石头厚重。
我们还可以用几何图形对比。一个正方形 显示的质感比三角形要厚重,圆形也比三角形厚实,而圆形又比正方形无邪 。圆形既有一种内缩力(向心力),同时又有向四边流动的趋势。在圆形的较量 下,正方形显得虽厚重却鸠拙。因此,圆形的特征 是书法美的组成中既不失厚重(问心力,又显示流动的最理想的性格。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金石文字中的大篆体在篆、隶、楷三种基本字体中最趋近于圆的性格(线的圆性);厥后的行草书线条多为细尖, 虽在结构上靠近 于圆的特征,但线条缺乏一种向心力,泰山金刚经的每一点画边缘多为圆势,使其自身显出一种凝重之感。
另外,圆性的线条(非指外部运动形式的曲化),还能生就逐一 种蕴藉。唐时及厥后的楷书已刻意将线条锐化(如颜、柳楷字),已经没有南北朝时的蕴藉(边缘的圖化及模糊)。同样拿泰山金刚经与石门铭较量 ,金刚经更近蕴藉简静。
虽然,在线条形式中,纯圆形过多的圆形线条会显得单调。在不失厚重的条件 下,将方形与圆形对比则更显出线条的无邪 来。张迁碑即是一个很好的规范。
(3) 渺茫
“天苍苍, 野茫茫,"自然界渺茫 的景致美不胜收。渺茫 给人以扑朔迷离的感受,金石文字由风化而成的渺茫 使其飘然欲仙,把浏览 者带入一片幽玄的田地 。
书法线条的渺茫 有两种,一种是单质的老化而成的渺茫 ,类似虚弱病人徐徐垂暮,老而昏化。刘熙载曾担忧书之苍者易“涉于老秃”,申饬我们欲苍必先有“深”意。依我的明确 ,刘氏此“深”意即渺茫 的实体必须深挚 ,只有在雄厚基础上的渺茫 才是深不行测的。这第二种的渺茫 即是金石气的本美。
渺茫 在墨迹文字大多是以枯涩的字迹显露的。这是一个考察用笔熟练与否的问题 。没有深挚 的功夫,绝难至达渺茫 的境界。书之境以“老”为上,故有初学者以渺茫 写老,殊不知渺茫 乃功力之自然吐露 ,不行恣意 为之。线条不是在雄厚的基础上滋生的渺茫 ,则纯粹是一种枯秃。
历史上能得渺茫 者,一定为大手笔。颜鲁公行草,邓石如行草,吴昌硕所临散氏盘金文(吴氏石鼓文尚只雄厚,其行草则只是刚健)。今世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都是由雄厚而入渺茫 的。特殊之处,便在于此。
金石文字的渺茫 ,已如前所述。它差异于墨迹文字,在于它有一种整体的效应。苍多在局部,茫则漫无边际。至渺茫 ,金石气已多数形成了。
自阮元等提倡碑学以来,千古承袭的帖学之风一落千丈,书家们把北朝的书体奉为楷模。于是,碑学蔚然成风。然细细检核这几百年碑学实践,岂论是邓石如照旧晚清的康有为,都只将自己树于帖学的对立面,似乎碑学与帖学是水火不相容的。诚然,唐以后的帖学书法已经没有晋人矩度,越来越趋入靡弱。但碑学书家们一味攫取雄强,而忽略了对细微的追求。现实 上,金石气除却雄浑这个主特征外,尚有 一个十分主要 的组织因子,那即是古朴。
(二) 古朴
自然界的物质,由于时间的久远,在履历 摩擦、天气 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后,从外貌至内部都市有一种消耗 。我们看到未经人工刷新 的原始岩石在受长时期自然侵蚀 后的形象,其外部特征柔和而圆润,千年古松,万年枯藤,时间使其性格变得坚韧。一小我私人 工制作的新式样(艺术品除外),绝不会有古朴一类的特征。金石文字,历经风化,其线条外部边缘一定是柔和的,纵然泛起一些较方的角,其角度的过渡也极为自然,决不像唐后有些未经风化的碑文或墨迹文字的刻意角化。柔和使线条返归自然,掩饰了人工雕琢而生的烟火气。
中国的字画 艺术体现的古朴,反映出艺术家们对自然美的追求。赵孟頫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仔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作所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谓知其道,不为不知者说也。”倪瓒这样评价米带书法:“米老虽追纵晋人绝规,其气象弩张,如子路未见孔子时,难于伦比也。”(《倪瓒题蔡忠惠公十帖)》)中国的古贤人 老庄即招呼人们回归自然,其中虽含有某种消极的因素,但不无对自然美的憧憬。庄子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林”的美学头脑 一直是指导艺术实践的一个至理名言。
就书法来说,古朴直接体现在结字及线条上。结字的拙、简,组组成朴的内容,柔和、虚静的线条古意横生。
(1 ) 拙
拙和巧是一对矛盾,这是从普遍意义上说的。处在矛盾一面的拙是粗笨粗劣的意思,而另一面的巧则蕴含着人类的智慧。二十世纪的科学从宏观与微观方面都已经生长到祖先 不敢想象的田地。细菌实验,卫星上天, 人们听后一点不会感应惊讶。由拙到巧,意味着人类的前进 。在艺术生长来说,原始人或处在原始艺术阶段的人们尚没有很高的审盛意 识和实践履历 ,因此,他们“作品”往往很稚拙,无艺术原则可循。艺术形式的由拙到巧,批注 艺术由自在向自觉阶段的过渡。
原始时期的“作品”虽然很稚拙,但仍有许多美的因素。这种美是无意识的。这和我们审阅 儿童绘画并能发现其足资我们借鉴的工具一样。好比说,儿童绘画中的自然率真,正是理性的我们所缺少的。虽然,原始时期的艺术之以是 还称不上真正的艺术,在于其对一样平常 的巧的纪律的不熟悉 。现在天的我们则必须在巧的基础上返归自然,以求得自然之上的自然。
于是,拙重新被抬了出来。可是 ,这个被重新抬出来的“拙”已非昔日面目,它已经履历 了“巧”的历程,是比“巧”高一个条理的形式。
以是 ,孙过庭这样总结书法美的实践,“初学漫衍,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险绝是巧,复归平正绝不是简朴的回归,而是大巧而入拙。
然而傅山先生却呼出了“宁拙毋巧”的口号, 令后众人 费解。我想,傅先生所说的“拙”一定不是原始人或儿童的稚拙,否则艺术一定属于原始人或儿童了。但拙又怎能和巧对立,求拙而把巧放弃?
再回到理性时代的唐朝。 书法史上习惯把唐楷看成楷模,所谓“尚法”。我不知道唐人对这“法”事实 怎样 明确 。曾有人把欧阳询称为“结构大师”,这结构大师的伟大之处或许就在其严谨吧。但仔细研究一下欧字,它不外是相当平正而已。不少厥后的书家曾奚落 过欧字的布算。作为楷字的生长,欧字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但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书体,仅仅知足 于这种匀称 平正,则又有几多美可言?
历史的巧合使人们对隋唐以前的书法另眼相看。这种巧合即是字体演变历程中自然发生的结构的美。在两种尺度字体之间,其过渡的结构一定奇拙,不知巧而皆巧。清代碑学的兴起是为了阻挡其时帖学书法线条的蘼弱及结构的规范。而碑书作为书家们楷模的缘故原由 ,多数是在其结构的自然古拙。
(2 ) 简
艺术品是艺术家对生涯 和自然的高度提炼。原原本当地形貌 自然和生涯 ,艺术家似与摄影师无异。近现代西方艺术的醒觉 则集中体现在简约形式的象征性。中国艺术则险些从一最先 就基本具备了简的形式。
但纯艺术品结构的简约还差异于装饰艺术的简化式样。“艺术品所要诠释 的自然特征体现在多种力之间的重大 作用上,若是 艺术作品不能体现这种重大 性,就会导致僵化。若是 艺术品过份地强调秩序,同时又缺乏具有足够活力的物质去排列,就一定导致一种僵化的效果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使这种重大 的力结构趋于一种最纯净最明晰 的形式,这即是艺术品结构的简约。
书法是高度抽象的艺术。书法艺术结构的简约外貌上体现在文字的布白之中,而现实 上则是指线条的浓缩。只有浓缩的线条才气使文字结构简约。浓缩不是省略。简化字比之于繁体字只能说省略了某些笔画;尺度草书的结构则比楷书简化。两条质地、是非、粗细、姿态相同的线条,其力感是一样的。但若是 在长度上使其中一根浓缩,其他要素保持稳固 ,那么这根线条的内力便会加大。这是由于浓缩的线条密度变大的缘故。当一颗行星在其能量耗尽之时,其体积会显着 增大并爆炸。爆炸后的星体浓缩,成为黑洞。黑洞以其细小 的单元体积囊聚重大 的质量,因此在此外星体靠近时便会被它吞噬,其引力是何等重大 !
当我们将金石文字与后世的行草书较量 时,我们突然会有这样的发现:原本结构简化的行草书却比结构繁复的楷书、隶书要重大 得多。明清之际的草书比王羲之草书更多缱绻。过多的牵连使线条肩负加重,并使之简朴。“乱头粗服”的古代作品之以是 能迎合现代的学书者,多由于其用笔的单纯:只要将线条连贯即是。缠绕不清的线条因其形体过长,一定不能有金石文字的内聚力。
金石文字在结构上果真简约,但由于历史的缘故原由 ,这种简约只体现在单个的文字上。由于众多的简约的文字有秩序地排列,使其整个章法简朴。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结字的简约在一些经书中尤为显着 。或许是经书的创作者其自己具备较高的素质的缘故。他们将通常 清淡简朴的头脑 直接融入书法之间,使书法洋溢出一种单纯超脱的气息。
(3 ) 柔
中国艺术是最崇尚韵味的艺术。范温《潜溪诗眼》日:“韵者,美之极”,“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谢赫《古画品录》六法第一条即是“气韵生动”。韵是形式美的一个标致。在书法来说,章法及结字的疏密转变 及线条的富厚多姿,组成书法特有的韵意。
在纯形式的线条来说,韵多以柔展现 。柔主要以曲动为特征。静态的直线难以给人有柔的感受,直折线则在视觉上造成逐一 种断裂。 急剧的运动虽能饱一时眼福,但总不比舒展柔和的女子自由体操或芭蕾更有韵致。帖之韵在线条的节律转变 ,而金石之柔,则在其风化后的直而有曲姿。
从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受我们可以发现:视觉上的直而有曲姿与听觉上的浑音或余音有些相似。一个女高音的尖叫无疑能给人震惊,但震惊后连忙 又回复清静 ,由于 尖啼声 调简朴,没有韵致。相反,当夜深人静之时,远方的钟声敲响,钟声之宏厚的颤音渐次向周围 扩散,其声色之宏之柔,回味无限 。就声音而言,女声听上去似乎比男声柔和,但细细体味,男音沉宏所发生的柔韵比女声响亮 所发生的柔的却要深刻得多。
线条同样云云 。以细微优雅为特征的帖书在金石文字线条的映衬下似乎显得不尽细微。简朴地以笔画为例剖析 。帖书的横直画多倾力于两头 的转变 。“一波三折”即是对这种转变 的形象归纳综合。帖画之韵则在这一波三折中发生。但“一波三折”却是个有限的行动。它有很强的划定性,即其提按必须凭证 文字结构的枢纽而举行 ,这种行动停留在笔画的两头 。若是 中央 也施以某种装饰,一定其貌不扬。一个显着 的典型是黄山谷的某些笔画。黄氏妄想 在线中造成某些运动,但效果 适得其反,太过的强调离异了线条的自然性。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不少临习金石文字的习作,作者们对线条的明确 也仅仅停留在表层。如临《石门颂》以扭动来体现原文玄妙 的律动,颇有东施效颦之感。帖画的“一波三折”转变 比金石文字的中截律动看似细微实则简朴。后者的律动是在顺一定偏向延伸的同时又向其双方 无规则的漫渗,若是 以提按行动来剖解 其轨迹的话,则是这么一个图式: 它差异于黄山谷的跳跃式行动,这是自然作育 的转变 ,没有帖书人工雕饰的匠气。这种无规则的玄妙 律动天生 了其弘大深邃的质体,也显扬出差异于帖书规则顿挫而生的柔韵,而其韵之足,着实 帖书有意顿挫之上。
我们还可以从钢笔字与毛笔字的对比诠释 金石文字线条的富厚性。陈振濂先生在《线条运动的形式》一文中对之作了较量 。陈文说:“用钢笔齐整 根线与用毛笔按笔法画一横,两者都有‘时间’流动、推移的性格,但前者只体现一种‘绵延时间’的内容,尔后者却会由于它的提按顿挫行动组成‘结构时间’的内容,亦即是说它不只在时间的刻度上标明自己所破费 的长度,而且还标明此举所具有的特此外质”(质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陈氏是想以钢笔与毛笔的较量 说明“书法艺术(毛笔)的魅力”。但陈氏以“提按顿挫”为条件来说明毛笔与钢笔质的差异,显然理由不尽充实,由于 现在的钢笔书法同样考究“提按顿挫”,同样也有节奏转变 。现实 上,钢笔终不及毛笔的体现力,在于钢笔字难以有一种渗透力,即我们所谓的文字 。它的轨迹总是一条单质的线(只管 也有提按)。当我们较量 帖字与金石文字时,则会发生相似的感受。帖书的“质”终不及金石文字。
包世臣对线条的中截之美曾有不少叹息。《艺舟双楫》这样说:“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头 ,而昔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行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头 收支使用 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以是 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更有以两头 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头 而玩其中截,则人共见矣。”金石之雄肆在其中截,其柔恰也在这雄肆的中截之中。金石线条内质的富厚性与自然性决议 其外态的柔和。
只管 碑学书家们眼见这种内质的律动,却很难在实践中将之体现出来。被包世臣捧为“神品”的邓石如篆隶书,虽其画之中截坚实不虚,也仍是一笔带过。何子贞妄想 以哆嗦来体现,却力显于外,失之做作。康南海则承袭“刷”笔,剑拔弩张,更无柔情古意。
另外,还须指明的是,线条曲化水平差异其柔亦有区别。一样平常 地说,坦荡的曲线比跌宕的曲线更有柔致,舒缓的行动比显着 的提按柔意更浓。唐人狂草,虽都是曲线,但多数失掉柔意,而为一种强烈 的形态(强烈 的形态虽也有韵味,但因其行动迅速,难以顾及线条的内质及线条种种形态的对比,使其整体显得单一而乏味)。因此,柔不完全与曲成正比。我们说“柔情似水”,当是指情爱中人委婉蕴藉的行动与心声,如水一样平常 ,而绝非急风暴雨之式。金石文字寓无限重大 的曲动于与之相对的直(非几何学中之直)的形态之中,更给人以无限 的魅力。
金石文字在雄厚简朴的质体上溢发出柔和与清润,终使其进入虚静空灵的境界。
金石气应属何种审美领域,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问题。
以一样平常 的形式而言, 美(广义)可以分为优美与高尚两种。 在中国则多以阳刚与阴柔分。在西方美学史上, 最早确立“高尚”这一看法的是古罗马的朗吉弩斯。但朗吉弩斯所说的高尚尚不列为审美领域来研究。真正有 意识地把高尚视为审美范酸并明确提出其美感心理特征的是英国美学家博克。博克把美与高尚坚决区别了开来。博克指出,美与高尚不仅其外部特征截然相反,优美的审美工具是小巧、柔和、谈雅、平滑、工稳、细腻、飘盈、纤弱等,而高尚却是笨抽、粗壮、重大 、阴晦 、貌寝、反面谐。而且,“它们确实是性子 十分差异的看法,后者以痛感为基础,而前者则以快感为基础;只管 它们在以后可能发生转变 ,违反 它们的因由 的直接天性,可是这些因由 却仍然使它们保持着永恒的区别。”《论高尚与美》)康德也说“美的愉快与高尚的愉快在种类上很不相同,美直接引起有益于生命的感受,以是 和吸引力与游戏的想象很能契合。至于高尚却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判断力批判》)。
把金石之美视作“壮美”或“高尚。”看上去极为理所虽然。整个碑学时代的书论及书法实践都在追求与小巧工稳的帖学书风截然相反的“雄壮”心胸 。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古拙弘大”、“钢筋铁骨”、“爽健厉举”等等。作为碑学理论滥觞的傅山“四宁四毋”说,现实 上在招呼人们放弃工稳细腻,而去追寻拙、丑、支离、率真的高尚特征。侯开嘉先生在《清代碑学的成因及碑帖论战的辩析》(载《美术史论》1988年第二期)一文中则直截了当地说:“纤弱艳俗的气质是与碑学的审美意见意义 绝缘的,碑学书家们是在“壮美’的美学领域内体现自己的气焰 气焰 !”
但完全把金石气视作“壮美”或“高尚”,并不妥切。由于 金石气不仅仅只有“壮美”或“高尚”的审美特征。
近人王国维先生在优美与高尚之外,又列出“古雅”这一领域。王国维以为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行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由 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之故, 而得一种自力 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虽第一形式之本不美者, 得由其第二形式之美雅,而得逐一 种自力 之价值”。王氏把艺术品之“神”、“韵”、“气”、“味”视为第二形式者多,第一形式者少。并举例说:“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依王氏看法,金石气无疑属于这第二形式之美的。但金石气的发生并不是“人格诚高,学问成博”之人的缔造,却是由于自然的风蚀。这自然之美”又是可作为第一形式言之的。现实 上只有在人们真正熟悉 金石气的特征并体现在书法创作中,才算获得了真正的第二形式之美。
但“古雅”是个较量 模糊的看法。王国维在文中没有作明确的叙述 。金石气可视为古雅。“古雅”却有极宽泛的涵义。而且,从“古雅”的词义看,它似乎更偏于优雅协调 的优美特征。
我们再从“中和美”剖析 金石气的属向。
和西方美学偏于极端的美学观相比,中国则一直 主张阳刚与阴柔的协调 。这一类美学头脑 直接源本于《易经》关于阴阳之道的哲学原理。阴阳协调 而化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独阴不成,孤阳不生。以是 ,在艺术审美上同样保持了中和的这一审雅观 。如锺嵘《诗品》对曹植诗的赞叹:“节气奇高,词藻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历代书论也不乏对中和美的崇尚。如孙过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项穆《书法雅言》评各家信法:“智永世南得其(逸少)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自在 之度,李邕得其豪俊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萧洒 之兴,而失之惊....”,也是从中和美的角度评析的。
但中和美往往给人一个错觉,以为只是平和或偏胜。刚不能太过,柔也不行过多,这样两者才气相和。本师章祖安先生曾就此撰文指出:“一提‘中和’,马上令人想到这是中国的‘国学’,这原没有错。但若是 把中和美仅仅明确 为四平八稳、无过不及,优雅协调 ,却是极大的误解。只须稍微仔细地思量 一下,中和之美体现在昔人的理论与艺术实践中有极为富厚多彩的样式和不啻天渊的差异条理。”章师把中和之美分为三个条理:无过不及,协调 平稳,谓之平和,属中和美的最低条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资之所近”,突出地体现强烈的个性气焰 气焰 者,为偏胜;“对立面双方反向强化,又相互渗透,相摩相荡,相犯相惩,相生相克,相反相成”,“双方愈拉愈远,却又愈加巧妙 地更细密 地团结 在一起,是谓大顺。此乃中和美之最高田地 。”
让我们撇开传统书论的印象式品评 ,从视觉角度审阅 书法线质中和美的递进,以明金石气在书法美中的位置。
从钢笔书法或瘦金书的单质线到微具文字 意味的扁薄线条(如傅山行草书的某些线条),跨入秀媚与刚健两个阵营。秀媚如赵孟頫行草,刚健有李邕《李思训碑》等,刚健与秀媚相和而有小顺路 丽,遒丽者如书贤人 王羲之,历代书法精品中亦多有此类(结字美另当别论)。帖学时代对线质美的要求多以此为最。但刚健与秀媚并非刚柔至极。清中后期的碑学书家们从大量金石遗文中找到了比秀媚与刚健更进层的质体:清逸与雄厚。于是,遒丽再分为偏胜的两个方面。对立面越来越深,越来越远,但又巧妙 地团结 在一起,清逸与雄厚相合而为清雄。清雄为大顺的低级阶段,清雄再至极地,终得苍雄而柔润。苍雄而柔润者,正是金石气之本质。
以上剖析 ,我们可以看出,金石气凝聚了优美领域的柔和、清雅、细腻、圆润、舒缓、玄妙 等特征及高尚领域的坚实、重大 、郁壮、拙朴、甚至貌寝。金石气宏壮的质体,同时又显出优美的姿态,看似极刚,又极其柔润,这是真正的大顺。项穆以为独王右军是大成,王字那里 显其弘大、郁壮、拙朴?张怀瓘奚落 “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也不无原理。
故《老予》日“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顽强 者莫之能胜。”至柔者却能驰骋于至坚。着实 ,刚之极者必以柔显,不是至柔之刚终不为至刚。所谓“内刚外柔”者,决非刚柔的简朴组合,而是统一 个质体同时给人的两种绝然相对的感受。
金石气属于至刚至柔的大顺之美。
1990年
接待关注诗字画 印条记,天天 发送专业的诗字画 印知识。

